
Sign up to save your podcasts
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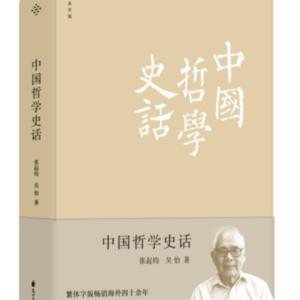

孔子的思想深厚圆融,面面俱到,真不知从何说起才是。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说孔子的中心思想便是“做人”。
人,生来已经是“人”,何必还要“做人”?原来我们生下来圆颅方趾,五官四肢,那只是自然界中的人,那只是动物
的一种,而不是我们自命为万物之灵,与天地参的“人”。“自然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用不着去“做”,而一个有意义,值得我们自傲的“人”,却须经过努力而获得。我们既秉受了人形,就应该把人所特具的宝贵性能尽量发挥出来,好好地做一个像样的“人”,而这一番自强不息的努力,就是“做人”的功夫了。
“做人”要“做”到什么地步,孔子给我们选 了一个目标是“仁”。只有“仁”才是人的最高准则。“仁”是什么?朱子说:“仁者本心之全德。”那就是说:仁是人的德性之总体,正因如此,所以“仁”的含义非常丰富,它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活动。说句老实话是“兼体用,赅本末”,绝不能用一个“定义”来表达,一如西方哲学之所为。(按:能下定义的,必须是一个概念,而“仁”则并不是仅仅一个概念。)大体说来“仁”的最基本意义是要对别人关切而爱护。例如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孔子告诉他:“爱人。”那就是说: “一个仁人应该爱护别人(而不是“人的定义是爱人”)。”所谓“爱”,是要等差的爱,是要我们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爱,而不是一律平等,贤愚莫分。我虽爱我叔父,但却更爱我的双亲;我虽爱我的邻人,但却怎能比我叔父;我虽当爱众人,但对于仁者却应更加亲近。这种态度,从表面上看好似胸襟褊狭,有失大公无私的气度,但如仔细想想,这不仅是最切实能行的途径,而且还正是本心最合理最真诚的反应。因为爱终究是一种情感,情感是在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而不能凭理智来制造。我们无法对不同关系、不同接触的人发生同样的感情。假如一定要同,那不是矫揉造zao4作,就势必是别有用心,那还有什么意义?反之我们若把内心的真实状况诚挚地表现出来,那才是真正的直道。以上是就理论来讲,再就事实来论,要对众人一体看待,说着虽然好听,实际上却根本行不通。试问我们如何能把父亲看成路人,或是把路人当作父亲来侍奉?反之我虽只侍奉我的父亲,但别人的父亲也正由他自己的儿子去侍奉。人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便能使这社会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爱”只是主观的情感,但仁者的爱人不能只凭主观情感,而要使这一腔热情真能发生效果,还须有适当的表达方式。因此当颜渊问仁时,孔子便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礼就是社会上的行为规范,复礼就是使我们的行为符合社会上公认的规范。以小事为喻,从前中国实行作揖、叩头,你如对某人表示敬爱之忱,作揖叩头就行了。假如你是去拥抱亲吻,那后果就不堪想象。因此只有通过社会的规范,才能真正达到我们爱人的目的。社会上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就是伦常(五伦),只有在伦常的践履中才能实现仁者的愿望。换句话说,一个深明大义的人绝不是从事妇人之仁、姑息之爱,相反的是要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尽到社会的责任,表现群体的大爱,然后才发挥了仁的精神,实现了“做人”的
意义。
上面这一套就是人生的行谊。我们束发受书,投师就教,学的就是这一套。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好的什么学?好的就是这一套。试看其诠释“好学”所说的“不迁怒,不二过”不就是这一番“做人”的努力吗?不仅坐而学是这套,起而行也完全是这一套。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那么求的是什么?求的就是“做人”的道理。这“做人”的道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离去。所以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切事,是做?还是不做?是取?还是舍?全都以“做人”的道理为依归。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假如心安理得,所行合乎“做人”的道理,怕是一种最贫困、最清苦的生活,也怡然自得,安之若素。所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反之假如违背了“做人”的理,即使是最优裕、最可羡的生活,也毫不加以考虑。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岂止如浮云?假定一旦走到这种地步,要“做人”就不能活命,那么一个有修养的人,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做人”的途径,绝不为活命而改易奋斗的方向。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什么?须知你若苟且偷生,生命虽是保全,但却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活着也不过是一个人形的动物而已。所谓“衣冠禽兽”者是。反之若是明辨是非,慷慨就
义,你虽失去生命的躯体,但却光荣地完成了人生的旅程,有血有肉地表现了“人”的存在。这时才真是尽到了“做人”的道理,而使“仁”的精神发扬光大,照耀人间。
个人如此,整个社会更要如此,否则岂不成了动物世界,禽兽集团?因此立国为政,一切都要本乎道义,所谓“政者,正也”。我们固然要谋求福利,使得国富民裕;但更要讲求人生的价值,“做人”的道理。所以当冉有问:“假如一个国家已经富了,还要怎么办?”孔子就告诉他“教之”,教什么?要教大家明人伦,敦礼义,而使国家高尚合理,不愧为一个人类的团体,这才是我们为政经邦的无上原则。国可破,家可亡,而这一原则却断断不可放弃。有一次子贡问政,孔子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兵”可去,甚至“食”都可去,但这代表道德正义的“信”却绝对不可去。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岂仅“不立”,那根本就不成其为“人”的国家了,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绝不以任何代价出卖信义,也不以任何借口放弃“做人”的原则。我们环顾今天世界各国,无不“唯利是图,唯力是视”,往往为了一时的便利,不惜出卖盟友,背弃信义,真不知立国的精神何在?假如大家,尤其若干大国,能奉行孔子的教训,坚守信义的原则,世界纵然未能获致永久的和平,至少也不会是今天这种混乱纷扰的局面了。
 View all episodes
View all episo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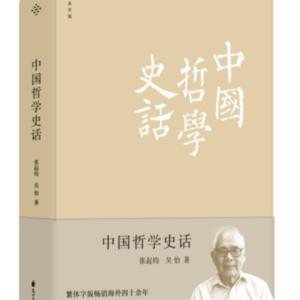 By 天山揽月
By 天山揽月
孔子的思想深厚圆融,面面俱到,真不知从何说起才是。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说孔子的中心思想便是“做人”。
人,生来已经是“人”,何必还要“做人”?原来我们生下来圆颅方趾,五官四肢,那只是自然界中的人,那只是动物
的一种,而不是我们自命为万物之灵,与天地参的“人”。“自然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用不着去“做”,而一个有意义,值得我们自傲的“人”,却须经过努力而获得。我们既秉受了人形,就应该把人所特具的宝贵性能尽量发挥出来,好好地做一个像样的“人”,而这一番自强不息的努力,就是“做人”的功夫了。
“做人”要“做”到什么地步,孔子给我们选 了一个目标是“仁”。只有“仁”才是人的最高准则。“仁”是什么?朱子说:“仁者本心之全德。”那就是说:仁是人的德性之总体,正因如此,所以“仁”的含义非常丰富,它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活动。说句老实话是“兼体用,赅本末”,绝不能用一个“定义”来表达,一如西方哲学之所为。(按:能下定义的,必须是一个概念,而“仁”则并不是仅仅一个概念。)大体说来“仁”的最基本意义是要对别人关切而爱护。例如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孔子告诉他:“爱人。”那就是说: “一个仁人应该爱护别人(而不是“人的定义是爱人”)。”所谓“爱”,是要等差的爱,是要我们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爱,而不是一律平等,贤愚莫分。我虽爱我叔父,但却更爱我的双亲;我虽爱我的邻人,但却怎能比我叔父;我虽当爱众人,但对于仁者却应更加亲近。这种态度,从表面上看好似胸襟褊狭,有失大公无私的气度,但如仔细想想,这不仅是最切实能行的途径,而且还正是本心最合理最真诚的反应。因为爱终究是一种情感,情感是在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而不能凭理智来制造。我们无法对不同关系、不同接触的人发生同样的感情。假如一定要同,那不是矫揉造zao4作,就势必是别有用心,那还有什么意义?反之我们若把内心的真实状况诚挚地表现出来,那才是真正的直道。以上是就理论来讲,再就事实来论,要对众人一体看待,说着虽然好听,实际上却根本行不通。试问我们如何能把父亲看成路人,或是把路人当作父亲来侍奉?反之我虽只侍奉我的父亲,但别人的父亲也正由他自己的儿子去侍奉。人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便能使这社会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爱”只是主观的情感,但仁者的爱人不能只凭主观情感,而要使这一腔热情真能发生效果,还须有适当的表达方式。因此当颜渊问仁时,孔子便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礼就是社会上的行为规范,复礼就是使我们的行为符合社会上公认的规范。以小事为喻,从前中国实行作揖、叩头,你如对某人表示敬爱之忱,作揖叩头就行了。假如你是去拥抱亲吻,那后果就不堪想象。因此只有通过社会的规范,才能真正达到我们爱人的目的。社会上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就是伦常(五伦),只有在伦常的践履中才能实现仁者的愿望。换句话说,一个深明大义的人绝不是从事妇人之仁、姑息之爱,相反的是要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尽到社会的责任,表现群体的大爱,然后才发挥了仁的精神,实现了“做人”的
意义。
上面这一套就是人生的行谊。我们束发受书,投师就教,学的就是这一套。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好的什么学?好的就是这一套。试看其诠释“好学”所说的“不迁怒,不二过”不就是这一番“做人”的努力吗?不仅坐而学是这套,起而行也完全是这一套。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那么求的是什么?求的就是“做人”的道理。这“做人”的道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离去。所以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切事,是做?还是不做?是取?还是舍?全都以“做人”的道理为依归。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假如心安理得,所行合乎“做人”的道理,怕是一种最贫困、最清苦的生活,也怡然自得,安之若素。所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反之假如违背了“做人”的理,即使是最优裕、最可羡的生活,也毫不加以考虑。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岂止如浮云?假定一旦走到这种地步,要“做人”就不能活命,那么一个有修养的人,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做人”的途径,绝不为活命而改易奋斗的方向。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什么?须知你若苟且偷生,生命虽是保全,但却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活着也不过是一个人形的动物而已。所谓“衣冠禽兽”者是。反之若是明辨是非,慷慨就
义,你虽失去生命的躯体,但却光荣地完成了人生的旅程,有血有肉地表现了“人”的存在。这时才真是尽到了“做人”的道理,而使“仁”的精神发扬光大,照耀人间。
个人如此,整个社会更要如此,否则岂不成了动物世界,禽兽集团?因此立国为政,一切都要本乎道义,所谓“政者,正也”。我们固然要谋求福利,使得国富民裕;但更要讲求人生的价值,“做人”的道理。所以当冉有问:“假如一个国家已经富了,还要怎么办?”孔子就告诉他“教之”,教什么?要教大家明人伦,敦礼义,而使国家高尚合理,不愧为一个人类的团体,这才是我们为政经邦的无上原则。国可破,家可亡,而这一原则却断断不可放弃。有一次子贡问政,孔子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兵”可去,甚至“食”都可去,但这代表道德正义的“信”却绝对不可去。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岂仅“不立”,那根本就不成其为“人”的国家了,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绝不以任何代价出卖信义,也不以任何借口放弃“做人”的原则。我们环顾今天世界各国,无不“唯利是图,唯力是视”,往往为了一时的便利,不惜出卖盟友,背弃信义,真不知立国的精神何在?假如大家,尤其若干大国,能奉行孔子的教训,坚守信义的原则,世界纵然未能获致永久的和平,至少也不会是今天这种混乱纷扰的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