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gn up to save your podcasts
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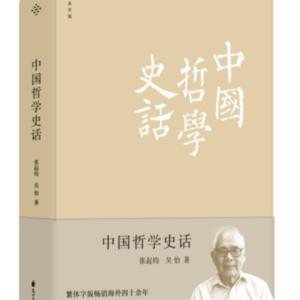

他的内心虽然满怀着深忧,但他绝不像孔子一样叹道穷, 也不像墨子一样大声疾呼,他却相反地付之一笑。他从客观的立场来看主观的我,觉得一切都是可笑的,他的一切忧愁、快乐都是可笑。试看他的妻子死时,他的朋友惠施来吊丧,看见庄子正直着双脚,坐在地上,敲着瓦盆在唱歌。惠施奇怪地问:“她和你相伴一辈子,生下的儿子也已成人。她死了,你不哭一声,倒也罢了;反而敲盆唱歌,这未免太过分了!”庄子回答说:“不如你所说,她初死时,我哪里能无动于衷呢?但仔细一想,她本来是无生无形,毫无踪影的;突然有了这个形,又有了生命,现在她又死去,这不正像春夏秋冬,随时在变化吗?她也许正在一间巨室内睡得很甜呢?我却号啕地接连哭着,自己想想未免可笑,所以也不哭了。”这是一种把悲观和乐观消融在一起的达观主义。
庄子临死的时候,也是那么的达观。他的几个弟子商量, 如何好好地安葬老师。庄子便说:“我把天地当棺椁,日月当连璧,星辰当珠玑,万物当赍ji1品,一切葬具都齐全了,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弟子们回答说:“没有棺椁,我们深怕乌鸦老鹰吃了你。”庄子微笑地说:“弃在露天,送给乌鸦老鹰吃;埋在地下,送给蝼蛄蚂蚁吃,还不是一样吗?何必厚此薄彼,夺掉这边的食粮,送给那一边呢?”
这是何等的达观,何等的境界!
 View all episodes
View all episo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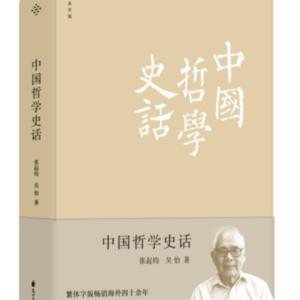 By 天山揽月
By 天山揽月
他的内心虽然满怀着深忧,但他绝不像孔子一样叹道穷, 也不像墨子一样大声疾呼,他却相反地付之一笑。他从客观的立场来看主观的我,觉得一切都是可笑的,他的一切忧愁、快乐都是可笑。试看他的妻子死时,他的朋友惠施来吊丧,看见庄子正直着双脚,坐在地上,敲着瓦盆在唱歌。惠施奇怪地问:“她和你相伴一辈子,生下的儿子也已成人。她死了,你不哭一声,倒也罢了;反而敲盆唱歌,这未免太过分了!”庄子回答说:“不如你所说,她初死时,我哪里能无动于衷呢?但仔细一想,她本来是无生无形,毫无踪影的;突然有了这个形,又有了生命,现在她又死去,这不正像春夏秋冬,随时在变化吗?她也许正在一间巨室内睡得很甜呢?我却号啕地接连哭着,自己想想未免可笑,所以也不哭了。”这是一种把悲观和乐观消融在一起的达观主义。
庄子临死的时候,也是那么的达观。他的几个弟子商量, 如何好好地安葬老师。庄子便说:“我把天地当棺椁,日月当连璧,星辰当珠玑,万物当赍ji1品,一切葬具都齐全了,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弟子们回答说:“没有棺椁,我们深怕乌鸦老鹰吃了你。”庄子微笑地说:“弃在露天,送给乌鸦老鹰吃;埋在地下,送给蝼蛄蚂蚁吃,还不是一样吗?何必厚此薄彼,夺掉这边的食粮,送给那一边呢?”
这是何等的达观,何等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