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gn up to save your podcasts
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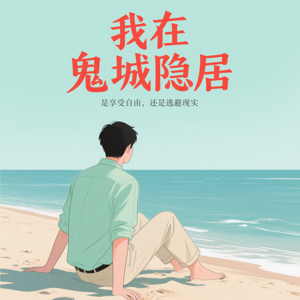

夜深人静,海浪声像远方的呼吸。我偶尔会做一件很“危险”的事——翻看手机相册里,前三年在乳山银滩拍下的照片。
我特意点开那些冬天的相册。2022年的冬天,2023年的冬天,2024年冬天我去云南和海南了。一张张看过去,屏幕的冷光映在脸上,我仿佛在看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照片的主角,总是我自己。或者说,是我自己在海边那个孤独的、小小的身影。
我穿着厚重的羽绒服,把自己裹成一个粽子,像一粒黑芝麻,被撒在无边无际的、洁白的沙滩和铅灰色的大海之间。背景要么是灿烂到近乎惨烈的落日,要么是刚下过雪的、空无一人的海岸线。
看着那个身影,连我自己都很难用言语去描述,我当初是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就敢一个人这样待在乳山银滩。
而且,是那种近乎决绝的“不和任何人往来”。
在北京七年,我需要“勇气”去应付酒局,需要“勇气”去面对KPI,需要“勇气”在拥挤的地铁里保持不倒。那种“勇气”,是外向的、表演性质的、消耗的。
而银滩的这种“勇气”,是内向的、真实的、自我滋养的。它不是让你去“面对”人群,而是让你有力量“离开”人群,并且在离开之后,还能坦然地面对那个唯一的、赤裸的、无处可逃的“自己”。
我看着照片,试图钻进那个黑点儿的脑袋里去。
那张我迎着落日站立的照片,霞光万道,我到底在想什么?是在感叹“夕阳无限好”,还是在想“今晚吃什么”?
那张我在及膝的积雪上踩出第一行脚印的照片,我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是“独钓寒江雪”的诗意,还是仅仅在盘算“这鬼天气,雪什么时候能停”?
我发现,我回忆不起来了。
那些当时汹涌在心中的、或宏大或渺小的念头,都像海浪拍打沙滩上的字,被时间一抹,了无痕迹。
这就是照片的局限。你从一张照片里,永远看不出来一个人真正在想什么。你只能看到一个“姿态”,一个被定格的、沉默的瞬间。他的灵魂在呐喊还是在沉睡,你是不知道的。
而这种沉默的“独处”,总会让人不可避免地想起一个名字:梭罗。
我的书架上,那本《瓦尔登湖》已经被我翻得起了毛边。他是所有隐居者的“祖师爷”。
但是,我冷静地算了一笔账:亨利·戴维·梭罗,他于1845年7月4日搬进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于1847年9月6日离开。满打满算,两年两个月零两天。
他只在瓦尔登湖旁边独居了两年而已。
而我呢?我在乳山银滩,度过了三年,两个冬天,现在,第四年的冬天已经开始。我的“独居生涯”,在时间上,已经悄然超过了他。
我这么说,并非狂妄,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内心确实涌起一种复杂的、近乎自负的情绪。
我好像……真的比梭罗还要“厉害”一点。
我不是说我的文笔比他好,思想比他深邃。我指的是另一件事——我好像比他还要耐得住寂寞,还要更擅长“隐居”这件事本身。
我们必须承认,梭罗的隐居,是一场伟大的“行为艺术”和哲学实验。但这场实验,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他的小木屋离康科德镇并不远,他时常进城,他的母亲和姐妹们会给他带馅饼和甜甜圈。他有络绎不绝的访客,他在林中举办沙龙。
而我这几年的生活,尤其是在银滩的冬天,那种“寂寞”的纯度,可能比瓦尔登湖畔的还要高。
这里没有沙龙,没有访客。冬天的小区一片漆黑,整栋楼只有我一户亮灯。我有时可以一整个星期不说一句话,唯一的声音来源是海浪、北风,以及我给自己播放的播客。
在这种极致的安静里,我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津津有味。
梭罗在两年里,写出了一本不朽的《瓦尔登湖》。
我也在写作。
我不敢说我的文字能流传后世,但在“量”上,我绝对是压倒性的。我每天都在写,公众号、日记、随笔、书评。这三年多,我写下的文字,如果汇编成册,大概能摞起厚厚的一沓。
梭罗的写作,是集中的、精华的,是他在两年实验结束后,提炼出来的思想结晶。
我的写作,是流淌的、日常的,是我对抗虚无和寂寞的唯一手段。它不是我的“作品”,它就是我的“呼吸”。
我也在思考。
梭罗在湖畔思考自然、经济和生命的价值。我则是在海边,解开了许多困扰我前半生的人生疑惑。
比如,人为什么一定要“成功”?为什么一定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为什么我们总是活在别人的期待和自己的欲望编织的牢笼里?
在北京漂了七年,我带着这些死结来到海边。这三年,我像一个笨拙的渔夫,每天坐在海边,面对着这片空旷和虚无,一根一根地,把这些死结慢慢解开了。
我解开的答案很简单,简单到可笑:那些“结”,根本就不存在。它们都是“装模作样”的文明社会塞给你的幻觉。当你选择“不玩了”,那些“结”就自动松开了。
当我把这一切都想通透,再回头看照片里那个独自站在雪地里的“我”时,我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
我佩服他。那个在三十多岁,敢于按下人生暂停键、甚至退出键的人。那个在“鬼城”的空旷里,没有疯掉,反而找到了内在秩序的人。
而最关键的区别在于:
梭罗最后离开了瓦尔登湖。
他完成了他的实验,收集了他想要的素材,证明了他的观点。然后,他回去了,改变了生活方式,重新“融入”了他曾经短暂逃离的文明世界。他回到了康科德镇,做演讲,写文章,参与废奴运动。
他是一个入世的“隐士”。
而我,还想继续隐居在乳山银滩。我不想融入到那个人群中去。
我不是在做一场为期两年的“实验”。我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截止日期”。我不是为了写一本书才来到这里。
我只是单纯地发现,那种“装模作样”的人群生活,我过敏。而这种“无人问津”的独居生活,我上瘾。
我离开北京,不是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回归”——回归一种更接近我生命本质的状态。
现在,我回归了,我感觉很舒服。我为什么要再次离开呢?
所以,梭罗的两年,是一个伟大的“逗号”,是他精彩人生中的一个篇章。
而我的这四年,以及未来的五年、十年……也许,这会是一个“句号”。我不是在这里“体验生活”,我就是在这里“生活”。
也许,我会过一辈子这样的生活,而不只是两年的瓦尔登湖。
这片海,这片沙滩,这个“鬼城”,就是我的瓦尔登,一个更冷、更空、但也更彻底的瓦尔登。
 View all episodes
View all episo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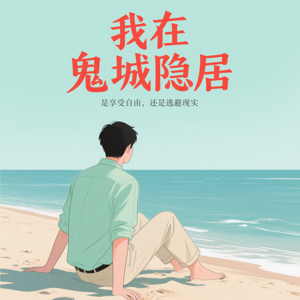 By 海边的第欧根尼
By 海边的第欧根尼
夜深人静,海浪声像远方的呼吸。我偶尔会做一件很“危险”的事——翻看手机相册里,前三年在乳山银滩拍下的照片。
我特意点开那些冬天的相册。2022年的冬天,2023年的冬天,2024年冬天我去云南和海南了。一张张看过去,屏幕的冷光映在脸上,我仿佛在看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照片的主角,总是我自己。或者说,是我自己在海边那个孤独的、小小的身影。
我穿着厚重的羽绒服,把自己裹成一个粽子,像一粒黑芝麻,被撒在无边无际的、洁白的沙滩和铅灰色的大海之间。背景要么是灿烂到近乎惨烈的落日,要么是刚下过雪的、空无一人的海岸线。
看着那个身影,连我自己都很难用言语去描述,我当初是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就敢一个人这样待在乳山银滩。
而且,是那种近乎决绝的“不和任何人往来”。
在北京七年,我需要“勇气”去应付酒局,需要“勇气”去面对KPI,需要“勇气”在拥挤的地铁里保持不倒。那种“勇气”,是外向的、表演性质的、消耗的。
而银滩的这种“勇气”,是内向的、真实的、自我滋养的。它不是让你去“面对”人群,而是让你有力量“离开”人群,并且在离开之后,还能坦然地面对那个唯一的、赤裸的、无处可逃的“自己”。
我看着照片,试图钻进那个黑点儿的脑袋里去。
那张我迎着落日站立的照片,霞光万道,我到底在想什么?是在感叹“夕阳无限好”,还是在想“今晚吃什么”?
那张我在及膝的积雪上踩出第一行脚印的照片,我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是“独钓寒江雪”的诗意,还是仅仅在盘算“这鬼天气,雪什么时候能停”?
我发现,我回忆不起来了。
那些当时汹涌在心中的、或宏大或渺小的念头,都像海浪拍打沙滩上的字,被时间一抹,了无痕迹。
这就是照片的局限。你从一张照片里,永远看不出来一个人真正在想什么。你只能看到一个“姿态”,一个被定格的、沉默的瞬间。他的灵魂在呐喊还是在沉睡,你是不知道的。
而这种沉默的“独处”,总会让人不可避免地想起一个名字:梭罗。
我的书架上,那本《瓦尔登湖》已经被我翻得起了毛边。他是所有隐居者的“祖师爷”。
但是,我冷静地算了一笔账:亨利·戴维·梭罗,他于1845年7月4日搬进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于1847年9月6日离开。满打满算,两年两个月零两天。
他只在瓦尔登湖旁边独居了两年而已。
而我呢?我在乳山银滩,度过了三年,两个冬天,现在,第四年的冬天已经开始。我的“独居生涯”,在时间上,已经悄然超过了他。
我这么说,并非狂妄,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内心确实涌起一种复杂的、近乎自负的情绪。
我好像……真的比梭罗还要“厉害”一点。
我不是说我的文笔比他好,思想比他深邃。我指的是另一件事——我好像比他还要耐得住寂寞,还要更擅长“隐居”这件事本身。
我们必须承认,梭罗的隐居,是一场伟大的“行为艺术”和哲学实验。但这场实验,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他的小木屋离康科德镇并不远,他时常进城,他的母亲和姐妹们会给他带馅饼和甜甜圈。他有络绎不绝的访客,他在林中举办沙龙。
而我这几年的生活,尤其是在银滩的冬天,那种“寂寞”的纯度,可能比瓦尔登湖畔的还要高。
这里没有沙龙,没有访客。冬天的小区一片漆黑,整栋楼只有我一户亮灯。我有时可以一整个星期不说一句话,唯一的声音来源是海浪、北风,以及我给自己播放的播客。
在这种极致的安静里,我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津津有味。
梭罗在两年里,写出了一本不朽的《瓦尔登湖》。
我也在写作。
我不敢说我的文字能流传后世,但在“量”上,我绝对是压倒性的。我每天都在写,公众号、日记、随笔、书评。这三年多,我写下的文字,如果汇编成册,大概能摞起厚厚的一沓。
梭罗的写作,是集中的、精华的,是他在两年实验结束后,提炼出来的思想结晶。
我的写作,是流淌的、日常的,是我对抗虚无和寂寞的唯一手段。它不是我的“作品”,它就是我的“呼吸”。
我也在思考。
梭罗在湖畔思考自然、经济和生命的价值。我则是在海边,解开了许多困扰我前半生的人生疑惑。
比如,人为什么一定要“成功”?为什么一定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为什么我们总是活在别人的期待和自己的欲望编织的牢笼里?
在北京漂了七年,我带着这些死结来到海边。这三年,我像一个笨拙的渔夫,每天坐在海边,面对着这片空旷和虚无,一根一根地,把这些死结慢慢解开了。
我解开的答案很简单,简单到可笑:那些“结”,根本就不存在。它们都是“装模作样”的文明社会塞给你的幻觉。当你选择“不玩了”,那些“结”就自动松开了。
当我把这一切都想通透,再回头看照片里那个独自站在雪地里的“我”时,我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
我佩服他。那个在三十多岁,敢于按下人生暂停键、甚至退出键的人。那个在“鬼城”的空旷里,没有疯掉,反而找到了内在秩序的人。
而最关键的区别在于:
梭罗最后离开了瓦尔登湖。
他完成了他的实验,收集了他想要的素材,证明了他的观点。然后,他回去了,改变了生活方式,重新“融入”了他曾经短暂逃离的文明世界。他回到了康科德镇,做演讲,写文章,参与废奴运动。
他是一个入世的“隐士”。
而我,还想继续隐居在乳山银滩。我不想融入到那个人群中去。
我不是在做一场为期两年的“实验”。我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截止日期”。我不是为了写一本书才来到这里。
我只是单纯地发现,那种“装模作样”的人群生活,我过敏。而这种“无人问津”的独居生活,我上瘾。
我离开北京,不是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回归”——回归一种更接近我生命本质的状态。
现在,我回归了,我感觉很舒服。我为什么要再次离开呢?
所以,梭罗的两年,是一个伟大的“逗号”,是他精彩人生中的一个篇章。
而我的这四年,以及未来的五年、十年……也许,这会是一个“句号”。我不是在这里“体验生活”,我就是在这里“生活”。
也许,我会过一辈子这样的生活,而不只是两年的瓦尔登湖。
这片海,这片沙滩,这个“鬼城”,就是我的瓦尔登,一个更冷、更空、但也更彻底的瓦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