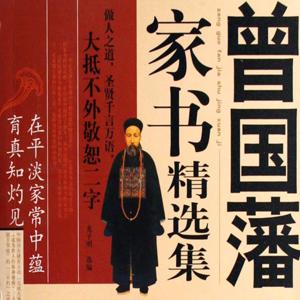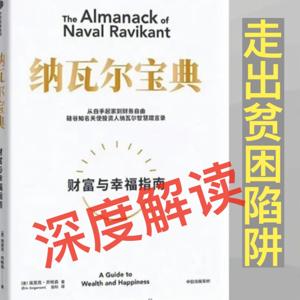第五十三篇 致两儿: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
【译文】
字谕纪泽、纪鸿儿:
泽儿在安庆、黄石矶、湖口所寄出的信,件件都已经收到。鸿儿呈递的连珠体寿文也已于初七收到。
我初九从军营出发到黟县巡查各岭的防务工作,十四日回归营中,一切都很顺利平安。
鲍超、张凯章两人的军队于二十九日、初四日获得了胜利后就再也没有与敌军作战。杨军门率领水陆军兵三千多人到达南陵,攻破敌军营垒四十多座,并救出了陈大富的军队。这是近日来最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
英国人已经接受安抚,我于九月六日奏请带兵北上增援的奏疏,现在已经奉旨不用前去。这段时间我将一心操办东南军务,家里人尽管放宽心。
泽儿看书天分很高,但文笔的功力却显得薄弱,说话又太随便,举止太轻浮。这次在祁门度过的时间太短,还没有改掉轻浮的毛病。今后必须要在言行举止方面时刻注意。鸿儿的文笔刚健,值得安慰和高兴。这次寄来的连珠文,先生为你改了多少字?总的体系是谁的见解?来信中要再次详细向我禀告这件事。
银钱、田产最容易滋长骄气和惰性,所以我家里千万不可积存过多的银钱,也不要置办田产,你们兄弟只要努力读书,绝对不怕没有饭吃。在此叮嘱。这次没有给澄叔写信,你们代我禀告他。
听说邓世兄最近读书有很大的进步,刚才看了祝寿的单帖寿禀,书法很是清晰圆润。现在我送去十两银子,作为世兄(汪汇)买书的费用。这次没有给寅阶先生写信,上次写信给他,请他明年继续留在家中教书,想必已经收到了。
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强调了银钱、田产最容易滋长骄气和惰性,所以家里千万不可积存过多的银钱,也不要置办田产,你们兄弟只要努力读书,绝对不怕没有饭吃的观点。由此可见,他将钱财看做是身外之物,如果积攒过多的金钱,那么儿孙就会因此而不再发奋读书,从此会骄傲懒惰起来。所以他力劝儿子要努力读书,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创造财富才是最好的治家之法。
怎样保持家道的兴盛呢?从上述家书中看,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给子孙留下大笔金银遗产。
一个人拥有了大笔钱财后,他的处理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一是自己用;二是赠送给亲人及他关心或心爱的人;三是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财产流向主要是后两种形式。至于他的遗产会产生何种结果或效益,那是他完全无能为力的了。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在他临死前处理好这笔遗产。很多拥有大笔财产的人在临终前煞费苦心,不为别的,就为遗产怎么处理。
给儿孙留下尽可能多的遗产,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人都在暗下决心的事情。普通人虽然也是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麻烦的是有些人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不但担心子孙生活遇到困难时会怨恨,会无法生存,而且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谁不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得好一点呢?可是,爱之实是害之,你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其中的道理何在?请看曾国藩的说法和做法。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写给各位弟弟的信中说:
儿子若贤,则不靠做官发财的收入或先人的遗产也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他将多造一孽,后来淫逸作恶,必将大大玷污家族的名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俸禄收入较多,除了父母的衣食之需外,则要尽量地周济亲戚族党之中穷困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认为,子孙拥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能力最重要。他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所以自立。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认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曾国藩说,如果子孙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斤斤计较一些细小的事情,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挽回了。明代的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说的就是品德不正,即使身处富贵,也要注定败亡的道理。
出于这种思考,曾国藩跳出了那个时代官宦人家以及一般人家富有之后都要买房置地的普遍行为,极力反对家中为他购买五马充私田之举。
不留钱财给后人,自古有之。如汉代三杰之一的萧何,位居宰相,但他买地建宅的时候却一定要找穷困偏僻的地方,治家也不修建有院墙的房屋。他说:“子孙如果贤德,会学我的俭朴;如果不贤,也会被人夺去田产。”无独有偶,晚清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说过相似的一段话,他说:“儿孙贤过我,留钱做什么?儿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曾国藩对此十分推崇,他说:“身居京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他还给其弟写信说:“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抱着掠取的期望,有动荡的时候也可避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
什么是正途?在曾国藩看来,读书才是正途。他在家书中常告诫子弟“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因此,曾国藩不留银钱田产给后人,却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书籍、文稿以及更为重要的精神财富。经确认,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内,藏书曾达三十余万卷,超过近代史上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山东聊城海源阁、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宋楼、杭州八千卷楼,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富厚堂藏书楼建于同治六年(1867年),分“公记”、“朴记”、“芳记”三部分。富厚堂藏书楼至今旧貌依稀,是中国保存至今的七座实构私家藏书楼之一。
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行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曾国藩没有左宗棠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说得很平和:“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家田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田产千万亩,亦仍归于无饭可吃。”
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属“高干子弟”,门庭显耀,却都未变成“衙内”或“大少爷”之类的角色,想来,其家教的影响和曾国藩对于子女职业生涯的规划和设计是主要原因。考究起曾国藩的后人,我们可以看到:长子曾纪泽诗文书画样样精通,还自学了英语,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家,声名远播,在处理西北边疆危机中,凭着“啮雪咽旃,期于不屈”的斗志和“酌情据理”的谈判艺术,舌战群敌,从沙皇贪婪的大口中夺回伊犁城,取得晚清外交上唯一的胜利;次子曾纪鸿,聪颖过人,酷爱自然科学,尤其在数学方面造诣很深,他“锐思勇进,创立新法”,并有《对数详解》等著作存世;孙子曾广钧是诗人,曾广铨是外交官,曾出使英、韩;曾孙曾宝荪、曾约农是教育家和学者,远近钦仰,足够叫人艳羡了。
曾家后人之所以如此“争气”,应该归功于曾国藩的教育有方,亦即“爱之以其道”。在继承儒家文化传统又深受近代湖湘文化精华影响的曾国藩眼里,子女职业生涯的发展规划与设计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设计有利于更好地让子女了解社会环境需要和个人的实力,实现社会环境、需求、个人性格、兴趣、能力与职业选择相匹配,有利于制订出有针对性的培养开发计划,鼓励自我掌控前途和命运,更好地实现人生目标。身在仕途而屡遭挫折的曾国藩比单纯士大夫更能体会为官和为士之感受,更清楚做学问与抓管理所需的能力之异同,也更明白尔虞我诈、陷阱遍地的官场环境氛围。他曾不是一个淡泊名利之人,年轻时汲汲于功名,在名利场历经一番角逐和磨砺后,他有着深刻的体会与反思,他说“多事之秋,多一人则重于泰山,少一人则弱于婴儿”,可见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为官之感。他秉承传统儒家文化“志为利禄,学者之大患也”的思想教条,也出于现实“明哲保身”的需要,恪守“进可读,退可守”的耕读思想,希望维持“考、宝、早、扫、书、蔬、鱼、猪”的耕读之家,反对子孙为功名利禄而学,希望子孙淡泊名利,做一个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他不求子孙升官发财,甚至不求其早日成名,唯求子孙做“读书明理之君子”,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告诫子孙“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为士之想”。有人曾总结其具体的成功经验有以下三条:
第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
第二,绝不为子女谋求“特殊化”待遇。
第三,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曾国藩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处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
由此可见,一个家庭长久的旺盛,与钱财的管理得当有一定的关系,如果钱财管理有道,那么才不会因财而惹起祸端,更不会因财而亡,那么家庭自然会处于长盛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