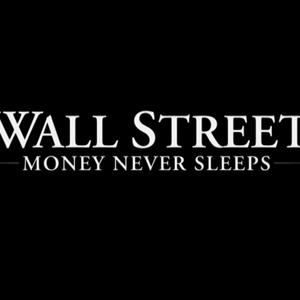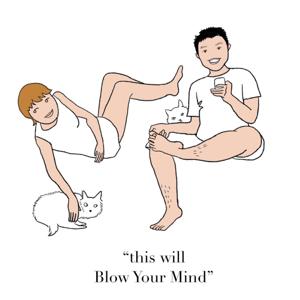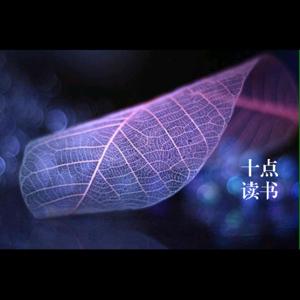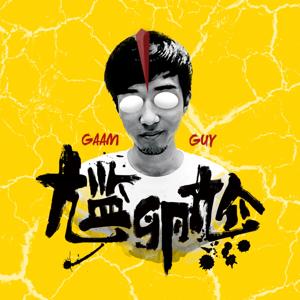渔人沿溪流蜿蜒而上,忽见一片桃花林,落英缤纷,芳草鲜美。复前行数百步,溪流尽头山岩上,一道裂隙把他引入奇异世界:安谧、祥和的平旷之野,屋舍俨然,稼穑丰茂,白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五世纪前期,陶渊明写了一篇著名的《桃花源记》。从此以后,中国人有了一种奇妙的情结,寄望如这渔人一般,发现不为人知的隐秘天地。这种想法长期盘踞在中国人心头,一个重要原因,是《桃花源记》亦真亦幻地描绘了一方净土。
渔人走出桃花源后,不顾村人的叮嘱,一路留下标记,并将此事详细报告太守。太守闻报,派人随渔人前往,标志尚在,但桃源已不知去向。一个名叫刘子骥的人听说了这件事,也打算去找,却因病未能成行。此后,遂无问津者。
《桃花源记》的结尾出人意料,因为这位刘子骥,历史上确有其人。
《晋书》记载,此人名叫刘之驎,字子骥,南阳人,生平最大爱好就是游山玩水。有一次,刘子骥采药至衡山,山林深处,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qūn,即谷仓),一囷闭,一囷开。由于涧水深广,刘子骥试了几次都没能过去,只好返回。事后,刘子骥听说那二石囷中都是仙灵方药等神奇事物,就想再去探寻一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地方了。
不需仔细推敲就能发现,刘子骥这段轶事,与《桃花源记》中渔人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陶渊明或许就是根据刘子骥的这段经历,创作出了《桃花源记》,又把刘子骥的名字放在末尾,以增强文章的真实性。
如果刘子骥的经历果真是《桃花源记》的原型,那么桃花源的所在似乎很明确——今湖南常德。《桃花源记》开篇写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太元,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当时的“武陵”即是如今湖南常德市武陵区。《晋书》称,刘子骥曾入衡山采药,衡山即在今湖南境内;《晋书》又说,刘子骥居“阳岐”,而阳歧在今湖北石首,属湖北省最南端,再往南,便进入湖南常德境内。
可惜,这个结论不能说服所有人,现在中国自称“桃花源”的所在有多处。考察这些所在,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南方,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带。
但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独辟蹊径,指出《桃花源记》的原型并不在南方,而在北方。在1936年发表的《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陈寅恪详细论证了这个观点。
魏晋之际,民不聊生。为避战乱,百姓常常聚族而居,在险要封闭的地方筑坞堡储粮,以求自保。东晋末年,参军戴延之随车骑将军刘裕自洛阳西征,撰有《西征记》两卷,其中提到了檀山坞、皇天塬等地名及掌故。恰好,陶渊明与这次西征的将佐不仅相识,还有诗文赠答。于是,陶渊明很可能从他那里直接或者间接听闻了檀山坞、皇天塬的情况,并据此写作了《桃花源记》。
陈寅恪最后得出结论:《桃花源记》虽是寓言,但也含有纪实的内容;其真实原型在北方中原的洛西地区,桃花源里的人民所避的“秦乱”并非秦始皇时代的战乱,而是与东晋并存的前秦之乱;陶渊明从《西征记》中得到启发,又把刘子骥入山采药的故事掺入到其中,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语,完成了全篇……
2010年秋意渐浓之时,我在洛宁县的洛水之畔见到了无数座坞堡,其中就包括檀山坞,檀山并不高,但四壁孤绝,堪称险要;山顶上,坞堡的痕迹早已消失;俯瞰山下,只见洛水一带依山而过,令人联想起渔人溯流而上的小溪。又在豫陕交界地带爬上数百米高的皇天塬,惊诧塬上竟然又是平原,绵延数十里,到处是果园和村落,果真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恰好还遇见一位老人领着孙女在田间挖草药,脑中也即冒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句子。
作家张承志先生曾说,桃花源的正名,或许是“桃花塬”。皇天塬的奇特遭遇也使我顿生相似的猜想:莫非桃花源不在幽闭的山中,而在高峻的黄土塬上?
当然,说来说去,终归都只是猜想,真正的桃花源在哪,恐怕只有去问陶老先生了。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1年第03期 作者: 舒波)
关注新浪微博 @中华遗产杂志 了解更多内容。 喵=3=





 View all episodes
View all episodes


 By FM1604421
By FM1604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