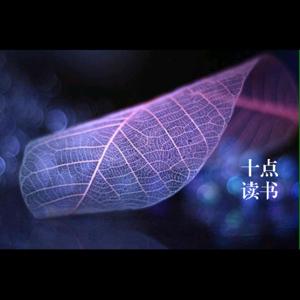提到“机关”,你的脑海里首先会浮现什么?是某种接近于暗器的装置,还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或者是“机关算尽太聪明”里的人的心思?
《列子.汤问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远在三千年前的西周,一个叫偃师的工匠给周穆王献上一具人偶。起初穆王以为是偃师的随从,不以为意。在得知这是偃师用木头造的之后,非常惊讶,把自己的宠姬也叫来一起观看。只见那偶人前进、后退、前俯、后仰,动作和真人无一不像。表演结束后,那偶人还向王的宠姬抛了抛媚眼。这一抛令周穆王勃然大怒,认定眼前的人偶一定是个真人,要将偃师当场处决。偃师急中生智,立刻上前将偶人拆开来给周穆王看。经过仔细“检测”,周穆王发现:它终究不过是一堆由木头和皮革组成、涂以胶漆和颜料的“死物”而已,偃师这才躲过一场杀身之祸。
在这个故事里,有意思的是周穆王检验它的方法:“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这实际是一种标准的科学方法:将伶人视为一个“黑盒子”系统,借由不同的“输入”与“输出”,推敲各种器官所主宰的功能。得出的结论是:伶人的心、肝和肾,分别在语言、视觉与步行这三项功能中扮演关键角色——从中我们已能约略窥见古人通过在假人里设置机关、以内脏控制肢体的秘密。
如果说西周因年代过于久远而更具神话般的色彩,那么从春秋战国直至汉魏,史载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开始可信了。三国时魏国的马钧被人称为“木圣”。他复原了众多过去只闻其名、未见其物的机关发明。史载,一个藩国向魏明帝进贡一种杂耍,名为“百戏”,明帝叫人把它装设在洛阳宫里,可安装完成后,众多木偶人却呆若木鸡,动不起来。明帝问马钧:“你能使这些木偶活动吗?”马钧肯定地回答道:“能!”明帝遂命马钧加以改造。马钧叫人购买了上等的木料,叫工人依照他设计好的图样,雕成许多整齐排列的木齿轮,同时建起一座大蓄水池,以水力驱动控制木偶的机关。当魏明帝前来观看时,只见木偶们有的击鼓,有的吹萧,有的跳舞,有的耍剑,有的骑马,有的在绳上倒立,还有百官行署,真是变化无穷。其巧妙程度比原来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杨广是一个颇遭非议的皇帝。除了大兴土木和荒淫无度之外,“玩物”也是其喜好之一。据说他因喜爱一个会讲故事的柳姓秘书到了极点,令人做了一个和柳一模一样的木制玩偶,摆在床头。这个木人的腹部装有机关,能够站起来、坐下去,并能行跪拜礼。每当在后宫夜饮,他就叫宫人把柳的木像放在桌上,供他玩耍。
据专给皇家修史的人说,这个奢华的隋炀帝,曾下令给自己修了座私人图书馆,叫观文殿,仅书房就盖了十二间。最特别的是门。它上挂锦幔,门后藏两个“飞仙”,在门口的地面埋设有机关。每当杨广驾临,就有宫人捧着香炉在前开路,在距离馆门一丈远的地方停下来,一踩暗钮,便触动机关——飞仙就降下来,手捧锦幔卷起,窗户立即打开,室内的书橱也同时开启。当皇帝的车驾返回宫殿时,门窗又都自动关闭,恢复正常。这所有的动作都是一个机关在控制。
机关之术发展到唐朝,估计已颇为普及,且花样繁多。比如郴州刺史王琚,用木头雕刻成一只木獭,将它沉到水里就能自动捕鱼,捕到鱼后便会伸着头颈浮出水面。唐朝武则天如意年间,海州向朝廷进献了一位匠人,能制造十二时辰车,其特别之处在于:当车辕转到正南时,午门便自动开放,有驾车的马与人从门里探身出来,比指南车更为先进。
以上总总,都提示了一个关键的进步。即:此时的木制机械,已经不只是按下开关后依照预先设计好的顺序自动运转了,而是能“分辨”外界的反应以进行自动调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智能”,这种智能有时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在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很细微的东西,它的状态的改变,影响并决定着整个事物的运动变化。这种东西就是“机”。《韵会》说:“机,要也,会也,密也。”在古代随处可见的机关装置里,正隐含着“机”的要义:是要害,是枢纽,是事物里秘而不宣的那部分。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无处不在,但最终还是存在于人的自身。人不仅可以创造出“机”,而且可以通过它,影响乃至驾驭自然。可以说,“机发”思想正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上一项重大成果,它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原理:“见微可以知著,用小可以制大。”这样,就从“几”的“见微知著”,发展到“机”的“以微制著”。
清朝末年,状元实业家张謇在家乡南通兴办新式工厂,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差人送去一副对联,上联书:“机枢之发,动乎天地”。这八个字极为精妙传神地传达了一个信号:中国儒生精英的观念正在发生自汉代以来最重大的转变——跳出个人内心,开始撬动外部世界。这一转变的触发点,正是“机”。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09年第04期 作者: 潜风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中华遗产杂志 了解更多内容~祝你晚安,好梦~=3=





 View all episodes
View all episodes


 By FM1604421
By FM1604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