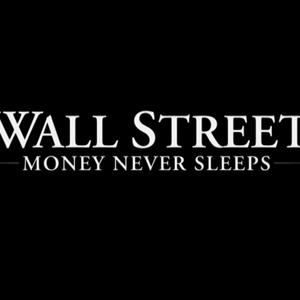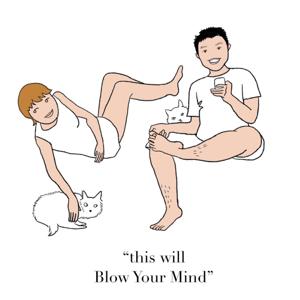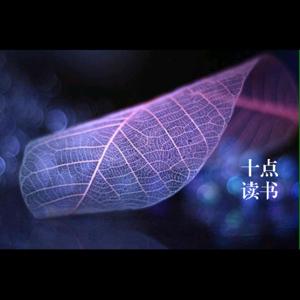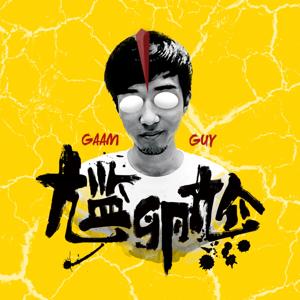培训“007”
国民党特务组织形成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反共“清党”期间,出于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考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相继出现。前者由陈果夫、陈立夫控制,后者的掌门人则是戴笠。
借着陈立夫的光,“中统”占了诸多人才优势,在谈到特情人员的出身问题时,他说:“我所知道的人,多半是美国留学生,学工程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所以调查科开始组织,就是请这些人帮忙参加,他们中没有一个懂得美国FBI或苏俄的‘格别乌’类似我们的调统工作的。我们的科分调查与统计两组,一面做,一面学……”
而戴笠方面亦不示弱。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笠,着手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在《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中,披露了早期针对特情人员开设培训班的情况:戴笠奉命担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以培训警官为名,培养特务。此校开设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训班,以政治和情报工作训练为主要课程。甲训班选派警校优秀正科生及各地特务骨干分子受训,专门培训高级特务人才;乙训班培训行动打手和充当警卫的专门技能,如骑马、射击、驾驶、武术(拳击、摔跤、擒拿等);丙训班招收十五六岁的女青年,训练科目除武术外,还授以女佣方面的技能,如缝纫、烹调、洗涤等,以为今后工作的掩护;电训班培训从事特工的无线电通讯人员。
通讯自古以来就是情报工作的生命,国民政府情报系统很早便将有限的精力和人力投注于无线电通讯领域。但无线电通讯无法采用物理隔离,你发出去的信号,理论上所有收发机都能听到,因此需要专门的加密电台和专业的情报人员进行操控。人才和设备便成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背后最大的支撑。
魏大铭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了破译加密电台的例子:“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后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
有了专业电讯人才,还得有给力的电报设备,才能如虎添翼。在浙江警官学校电训班,教官康宝煜很早就留意到当时情报人员使用的5瓦特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充电发电机体型太大,随身携带极为不便,于是便将收发报机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研制出一种小型收发报机。这种收发报机除去电池、听筒和电键外,只有两个饼干桶那么大,问题随即迎刃而解。
电台,无论对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说,都是心头肉,掌握无线电技术的专业人才更是稀缺资源。1933年,魏大铭以法租界的上海“三级锐电公司”为掩护,建立了“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把浙江警官学校的学员队长萧坚白调来当所长,更邀请了当时国际电台的报务长方砚农来当教务长,日以继夜培训无线电精英。这些学员日后绝大多数都投身抗日战线,就连一些中途肄业的,也被轮船公司、民用电台一抢而空。
有设备、有技术、有人才,国民党情报系统在对日作战中理应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基于利益诉求的不同,“中统”和“军统”两大系统攻诟不断,彼此倾轧,无端的内耗导致总体效能降低,而情报路线的错误,也引发了一连串的恶果。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04期 作者:赵恺 整稿:C先生
关注新浪微博 @中华遗产杂志 了解更多内容





 View all episodes
View all episodes


 By FM1604421
By FM1604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