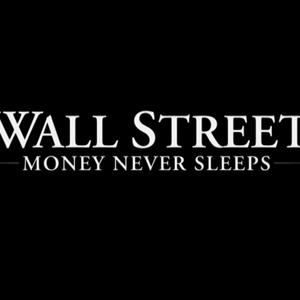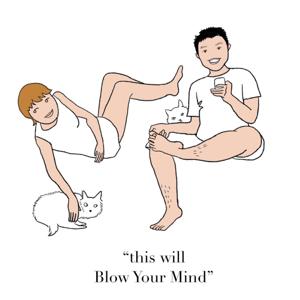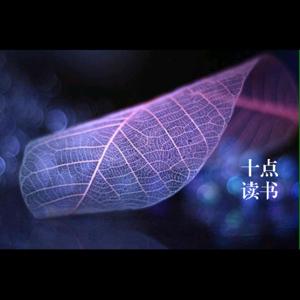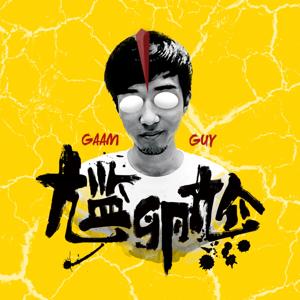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将要回国休假前,向清政府提议,由自己带几名中国官员一同赴欧,开拓一下眼界。恭亲王早有此意,即命满人斌椿率团出访,记录“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斌椿前后游历十一国,所见所闻写成《乘槎笔记》一书。他在出国的船上,看到外国丈夫服侍妻子,与他脑子里的“三纲五常”格格不入,让他惊奇不已。张德彝是斌椿使团的翻译,对西方礼俗也很不理解,看大街上男女牵手同行、宴会时男女杂坐,都极不以为然。至于节育,张德彝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将节育视之为“不孝”。对西方夫妇的一些正常举动,初次出洋的中国男人尚且以为惊世骇俗,那要同外国女子谈婚论嫁,简直是想也不会想。不过偶尔的艳遇,风流的中国书生倒不会拒绝。比如近代始游西方的林钺,接触不少热情的外国女郎,林钺感叹:“底事华蕃异致,黎倩牵心;天然胡妇多情,子卿谁是?”其实,访友、赠照,夜话,在西方,只是朋友间的正常交往而已。但西方女性这种出于礼节的举动,却常让“初来乍到”的中国人想入非非。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尽管是文化误读,却无伤大雅。对于当时的中国男人来说,洋妇只是新鲜有趣的插曲而已。不过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交往的加深,跨国婚恋却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外交官们做了中国近代跨国婚姻的“先驱”。1899年,当时在驻俄公使馆任职的陆徵祥,与比利时女子培德·博斐相识并成婚。而继驻外公使后,留学生也渐渐加入跨国婚恋一族。原本对此不闻不问的晚清政府,变得日益警惕起来。1910年,清廷出台一项法令:以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外交官与外国人结婚,必须向政府备案。清政府同时批准了学部要求限制留学生与外国人结婚的建议。清政府拨款给留学生,是希望他们在外国学习新知识,然后回国参与建设。如果一名留学生拿着官费出国,荒废学业后归国或学成而留居外国,在清政府而言,无疑都是浪费。放在台面上讲的理由,没有一点属于文化原因,都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然而跨国婚恋带来的文化冲突,却在台下愈演愈烈。比如对于近邻日本的女人,中国人也未必能够真正理解。以武侠小说成名的平江不肖生,写过一本百万字的《留东外史》。在小说中,一群中国留学生聚众赌博、被日本警察当场抓获。警官训斥他们:“你们贵国的留学生,也太不自爱了。”一个中国学生当场反驳,说赌博是世界通例。在《留东外史》中,作者还有这样的观点:“日本是个有名的卖淫国。要说绝对不曾卖过淫的,恐怕寻遍了日本,也寻不出一个来。”一个国家的女人都是妓女?这不科学。的确,日本人崇尚自然,耽于感官享受,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但把日本女子妓女化,却是中国人传统的性心理在作祟。有时候,这还与一种变态的复仇心和“爱国心”结合起来。东洋女子如镜中之花被扭曲丑化。西洋女子同样不被中国人理解。后来的新文化先锋胡适,就曾认为在女子地位上中国高于西方。在胡适看来,西方女子追求爱情,是一种“堕女子之人格”的行为。胡适与发妻江冬秀的婚事就是由双方家长决定的。我相信,在胡适写下上述日记的第二年,也就是1914年结识美国姑娘韦莲司后,他的想法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韦莲司是胡适所在的康奈尔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读书多、有文化,气质出众、胸襟开阔。初相识时,韦莲司问:“你好像不喜欢和女士交际?”胡适有些拘谨地回答:“也不全是,我和中年以上的女士还是有交往的。”韦莲司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自己“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是个又丑又无风韵的女人”。不过她无疑让胡适感受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两人的关系,大约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友情以上、恋人未满”。当然在跨国婚恋中,不只有中国人才会曲解对方。外国人的误读有时更蛮横霸道。晚清士人胡继曾与海伦的爱情故事,就惊动了英国领事。四川人胡继曾旅英期间与白人女子海伦相恋成婚并育有一双儿女。而胡继曾已有妻室。一个侨居成都的西方妇女,看到自己的白人同胞竟嫁给“东亚病夫”做了“妾”,不禁大为光火,寄书英国驻成都领事,告胡某有妻另娶,犯了重婚罪,要求领事出面,让当地政府判处胡继曾与海伦离婚。领事收到信后,即给代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致函。王人文以中国法律解释胡继曾同时娶两个平等的妻子是没有问题的。这位领事没有办法,只好把事情上报给英国驻华公使,但海伦始终不为所动。大清律与西方的婚姻制度发生了冲突。然而这只是表象。当时的《大公报》则上升到国家的高度: “英领事强以国际问题牵涉,逼令胡郝氏离婚,质言之强国妇女不肯嫁于弱国人民,而弱国妇女尽可作强国人民之妻之妾之玩物!”简单的婚恋问题,竟事关国家尊严。这并非中国人太敏感。近代以来,天朝 “不断沦落”,而欧美白人的优越感却“蒸蒸日上”。具有“正统思想”的白人对同胞嫁娶黄种人百般阻扰。为了维护国家和种族的“尊严”,大英帝国对在华英侨的婚娶严格要求。一旦有白人男性“犯禁”,选择跨国婚姻,就会成为社交圈中的异类,甚至等于自毁前程。1927年上海工部局警官Parker,娶了一个被认为“双亲是有身份”的中国女子,于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 女子在这个问题上面对的阻力更大,一个名为Tinkler的英国男子在给妹妹的信中警告说:“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曾负有一项职责,就是劝阻英国女子嫁给华人。婚恋一跨国,带来种种冲突和误解;婚恋一跨国,又牵涉着敏感的国家和种族神经。有些人成为直接受害者,比如混血儿。1892年,有一个日本人给英国大学者斯宾塞写信,请教他对跨种族婚姻的看法。斯宾塞在回信中以美国排华为例表现出其对跨种族婚姻的反感、对混血儿的歧视,这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当时无论中西方,种族观念都很强烈,都注重种族的纯洁性。1882—1891年的《上海海关报告》中曾讨论中国人不喜欢混血儿的原因。中国人对混血儿的抵制,根源于传统。而西方人则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大多数人都瞧不起混血儿的年代,打破隔离的努力却以“异想天开”的方式开始了。19世纪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痛感国家落后、世界不公,开始鼓吹跨种族通婚。康有为即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实现人类之“平等大同”,需先“人种大同”。他主张对不同人种“杂婚而化之”,如“黄、白相交而优其种”。康有为还只是设想,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李石曾则身体力行。据青年党创始人之一的李璜回忆,李石曾曾帮助一个青年华工与一个法国少女保住“世界大同的宝贝种子”,反对少女堕胎,帮助青年华工获得侨民身份,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李石曾后来专门筹款,开设了一个混血儿托儿所,用来收养中国工人、留学生与法国女性所生的孩子。如今的混血儿非但已无人歧视,甚至还成为被羡慕的对象。在大众印象中,混血儿聪明、漂亮,某种程度印证了康有为、李石曾的“改良种族”论。不过问题并没有终结。即使在今天,只要涉及跨国、跨地区、跨群体的接触,相伴的误会与冲突仍无法消停,跨国婚恋自然也不例外。世界似乎联成了一体,人们却未必相互理解。也许理解的第一步,就是渴望去理解的善意。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第4期 撰文/杨津涛 稿件整理:江离关注新浪微博 @中华遗产杂志 了解更多内容





 View all episodes
View all episodes


 By FM1604421
By FM1604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