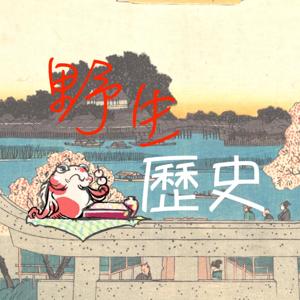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位老師,成大歷史系的林瑞明教授,在台灣文學界,他以林梵、梵音的梵這個筆名行走江湖。林老師是台南人,先後就讀成大歷史系跟台大歷史所,台大期間,因為修了詩人楊雲萍的課,感受到台灣文學的魅力,後來,又去拜訪了住在台中的楊逵,林老師研究所畢業之前,甚至跑到台中跟楊逵一起住了一年,後來寫成了《楊逵畫像》這本書。
也是在楊逵、這位集社會運動者與文學家於一身的前輩影響下,林老師認識到了賴和的重要性,但他當然沒想到,自己會在多年後擔任了賴和全集的編纂者。
楊雲萍、楊逵與賴和,啟發也堅定了林瑞明老師對於台灣史、台灣文學的研究熱忱,在他研究所畢業後,回到母校成大任教,也就一生都不曾再離開台南。在戒嚴時代,要以台灣文學為研究領域是一件危險的事,因此林老師常常得把台灣文學、台灣史藏在中國近現代文學或者中國近現代史的課程內,在當時的主流史學界,台灣史是一個相當邊緣的領域,常常受到質疑,被打壓也是常見的事,但林老師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於威權的反抗。
直到後來解嚴,風氣漸漸開放後,如何替台灣文學打造一個研究的殿堂,就成為林老師後半生努力的工作,2000年,成大的台灣文學研究所成立,2003年將舊的台南市政府改為國立台灣文學館,都是林老師在背後努力不懈地奔走、爭取、疾呼而誕生的成果。因為這些努力、因為有更多的青年學者加入,台灣文學研究、台灣史研究逐漸形成了體系,如果林老師是一個戀棧權力的人,他可以在這個體系中取得很高的話語權,但他在台灣文學館館長卸任後,就回到成大歷史系繼續教書、讀書,在他最心愛的台南走街串巷拜訪美食、找老朋友閒聊,將台灣文學與台灣史研究的火把交給了下一代的學人。
在我大學的時候並沒有修過林老師的課,但我們都傳說,林老師的研究室是奇幻的神之領域,每一個老師的書都很多,但林老師的書更是多到堪稱小型圖書館,而他總是端坐其中,我們從門外經過時常會聽見古典音樂流洩而出。
在我畢業後多年,有一天在FB上看到了老師的帳號,想說沒事就加一下,默默地成為林老師的臉友,偶爾在網路上留個言,後來我有一陣子在研究西川滿這位文學家,也想聽聽老師的意見,就跟老師約在吳園旁邊的十八卯茶屋聊天。老師聽完我的問題後,給我開了一個書單,我記得我問了一個很蠢的問題後,老師笑著說:「我是研究楊逵的,西川滿這樣的少爺,我當然對他比較沒興趣啊。」
楊逵與西川滿,可以說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兩個極端,一個是底層的台灣人、一個是高層的日本人,兩者的視角截然不同,而林老師的笑語也顯見了關注於底層、弱勢的心情。
在臨走時,老師送了我一本《日光與黑潮》,是由印刻文學出版的詩集。後來,再回台南時有時沒約好、有時沒約成,我就再也沒有跟老師見到面,直到2018年的年底,林老師在家中逝世,享年68歲。
那天我打開跟老師的對話框,對話停留在有一次我們討論到賴和,我說我不太懂詩,但賴和有一句詩我覺得很重要,「勇士當為義鬥爭」,老師打了三個哈哈哈,丟了一張賴和紀念館的匾額照片,正是,「勇士當為義鬥爭」。
因此,當我在規劃這個節目時,我想,我一定要讓大家認識林瑞明老師這樣的詩人、這樣的學者。所以,今天邀請的朗讀者,是一位總是全力以赴演出的演員、出道多年始終在追求更完美的演出。
請聆聽,金馬影帝莫子儀先生,為我們朗讀《日光與黑潮》中的篇章「時間哲學」與「生活」。
*選摘自,林梵,《日光與黑潮》,台北:印刻,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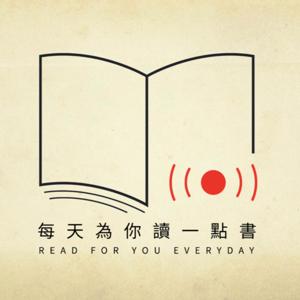

 View all episodes
View all episo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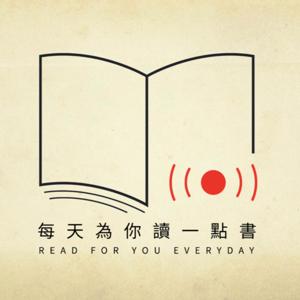 By 謝金魚
By 謝金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