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
王红
曹魏末年,嵇康被司马昭杀害。临刑前,嵇康将十岁的儿子嵇绍托付给朋友山涛(字巨源),安慰儿子说:“有山巨源在,你就不是孤儿。”
待嵇绍长大成人,天下已姓司马,魏变成晋。山涛向晋武帝举荐嵇绍,嵇绍正闭门隐居,想要推辞。山涛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天地运转,春夏秋冬都在不停地变更,何况人呢?希望嵇绍与时俱进,做个识时务的俊杰。嵇绍视山涛如父,听从了他的建议,出仕,在晋武帝、晋惠帝父子两朝为官。
晋惠帝司马衷是有名的弱智皇帝,他的天下自然觊觎者多。他做皇帝十多年,国家就没安定过。皇后作乱,兄弟叔侄互相攻打(八王之乱),惠帝只是个被不同人物捏在手里的傀儡。嵇绍在惠帝朝任侍中,忠心耿耿保卫着这个低能天子。
公元304年,东海王司马越奉惠帝北征,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与成都王司马颖激战。司马越的军队大败,百官与皇帝的侍卫四散奔逃,只有嵇绍临危不乱,端正冠带,挺身向前,用自己的身体为惠帝抵挡刀锋箭镞。乱军逼近皇帝的车驾,飞箭如雨般射来,嵇绍当场被杀死在惠帝身旁,鲜血溅了惠帝一身。战事平息后,侍从为皇帝换下血衣,昏庸的皇帝竟然说出一句明白话:“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去。”留下血衣作为纪念。
历史开了个沉甸甸的玩笑,41年前,在司马昭篡魏之心路人皆知时,嵇康坚持不合作的态度,为此付出生命代价,从容死在司马昭的屠刀下。41年后,嵇康的儿子也从容赴死,却是为了保卫杀父仇人的孙子,成了晋王朝的忠臣烈士。唐代人修《晋书》,嵇绍入了《忠义列传》,位居第一。
按传统观念看,嵇绍是忠臣,却又是父亲的不孝儿子。对这种矛盾,前人议论纷纭,顾炎武《日知录》的《正始》篇还据此阐发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意蕴。限于篇幅,此处姑且不论。但顾氏补充了一个例证:与嵇绍同时期,还有个叫王裒的人,因父亲王仪为司马昭杀害,坚决不仕西晋,授徒著书,隐居终身。同样的遭遇,不同的处世方略,让人不由得遐想:当年,嵇康为何要将儿子托付给山涛?假使嵇绍不是由山涛教养长大,又会怎样?
山涛圆通、善与时周旋,嵇康应是深知的,而山涛重情义和为人老成可靠又是嵇康深深信任的,所以他在写了那一篇尖锐淋漓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一定意义上是公开表示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宣言)后,仍将未成年的儿子托付给了山涛。阮籍不许儿子效仿名士放达的行为,高傲的嵇康在《家诫》中教儿子言行规矩,甚至庸碌。有谁能真正体会一个身处黑暗血腥时代的父亲的痛苦与无奈?
东汉党锢之祸中的范滂,慷慨赴死,毫无惧色,对未成年的儿子交代遗言时却沉痛惶惑、令闻者堕泪:“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恶绝不可为,而为善者却像我这样人头落地。孩子啊孩子,你的路该怎么走呢?
刑场上的嵇康,在抚琴弹奏《广陵散》时,内心是否也泛起过同样的惶惑与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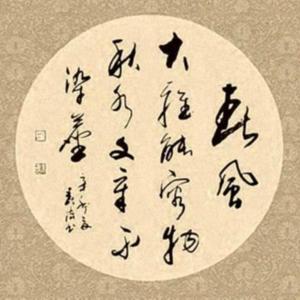

 View all episodes
View all episo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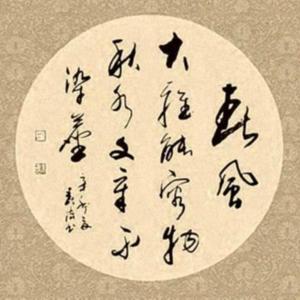 By 半井之蛙
By 半井之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