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gn up to save your podcasts
Or




FDA 连续批准2个治疗胆管癌的靶向药
Lancet 细胞海绵-三叶因子3监测法筛查Barrett食管
Nature 胃肠道也有独立的神经系统
培米加替尼(Pemigatinib)
约20%的肝内胆管癌患者存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2融合基因突变,培米加替尼(Pemigatinib)是一种选择性FGFR抑制剂。2020年4月,FDA批准培米加替尼治疗复发性的FGFR2基因融合或重排的局部晚期胆管癌。
《FIGHT-202研究:培米加替尼治疗晚期胆管癌的临床研究》Lancet Oncology,2020年5月 (1)
这个多中心、非盲、单臂、2阶段研究纳入FGFR2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胆管癌患者、其他FGF/FGFR基因突变的患者、和没有FGF/FGFR基因突变的患者肱146人。所有入组患者均接受培米加替尼治疗直到疾病进展、不可接受的毒性、撤回同意或医生决定。
中位随访17·8个月,FGFR2融合或重排患者中35·5%达到客观缓解(其中3例完全缓解,35人部分缓解)。高磷酸盐血症是最常见的不良事件,49%的患者在研究期间死亡,最常见的原因是疾病进展,与治疗无关。
结论:培米加替尼在以前治疗过的发生FGFR2融合或重排的胆管癌患者中均有一定疗效。
艾伏尼布(ivosidenib)
基因组分析表明,胆管癌中有13%的患者存在IDH1基因突变,艾伏尼布(ivosidenib)是一种新型的小分子靶向异柠檬酸脱氢酶1(IDH1)抑制剂。艾伏尼布2018年被FDA批准用于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一线治疗,2020年4月批准用于胆管癌靶向治疗药物。
《ClarIDHy研究:针对胆管癌异柠檬酸脱氢酶1(IDH-1)突变的新型靶向疗法的3期临床研究》Lancet Oncology,2020年8月 (2)
胆管癌是一种对化疗敏感的癌症。尽管吉西他滨联合顺铂的一线化疗是标准治疗方案,但二线治疗却效果有限。这项国际性、双盲、安慰剂对照的、随机的、3期临床试验中,招募了185例携带IDH-1突变的胆管癌患者,其中大部分患者原发性肝内胆管癌(90%~95%)伴远处转移(92%~93%),随机接受艾伏尼布或安慰剂治疗。
中位随访6.9个月时,艾伏尼布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优于安慰剂组(2.7个月 vs 1.4个月,P<0.0001)。因为本试验允许安慰剂组患者发生进展后,跨组接受艾伏尼布治疗,因此艾伏尼布组和安慰剂组的中位总生存期相似。虽然艾伏尼布组只有2%的患者达到客观缓解,但51%达到疾病稳定。最常见的严重不良反应是腹水。
结论:艾伏尼布是一种靶向IDH-1突变的药物,可改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并使疾病稳定。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gnitis,PBC),也称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是一种慢性胆汁淤积性、自身免疫性肝病,可导致肝硬化。病理特征是T淋巴细胞攻击肝小叶内的小胆管,胆管上皮细胞收到持续攻击,导致胆管逐渐破坏、消失。临床表现包括黄疸、碱性磷酸酶升高、转氨酶升高、血脂异常、抗线粒体抗体(AMA)阳性95%、抗核抗体(ANA)阳性70%。PBC治疗有2个目标:(1)治疗慢性胆汁淤积引起的症状及并发症:包括症状性脂肪泻、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甲状腺功能减退、严重高脂血症、贫血、消化道出血、肝硬化等需分情况处理。(2)抑制肝小叶内小胆管的破坏:病因治疗并不很成功,获批准的治疗仅有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 acid,UDCA)和奥贝胆酸(obeticholic acid,OCA);尚存争议的疗法包括秋水仙碱、甲氨蝶呤。
《GLOBAL PBC研究:提高PBC患者生存率的治疗目标》Am J Gastroenterology,2020年7月 (3)
虽然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胆红素和碱性磷酸酶被广泛认为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但是治疗目标应该是多少,与生存率的关系如何依据不足。文章作者采用GLOBAL PBC研究中的欧洲和北美中心的长期随访数据。
胆红素≤0.6×ULN的患者10年生存率为91.3%,胆红素水平大于0.6×ULN时,肝移植或死亡的风险逐渐增加。碱性磷酸酶正常的患者10年生存率为93.2%,在1.0-1.67×ULN之间的患者10年生存率为86.1%。
结论:当胆红素水平≤0.6×ULN或碱性磷酸酶正常的时候,患者发生肝移植或死亡风险最低,这对治疗目标的制定有重要的意义。
《病例对照研究:熊去氧胆酸治疗预防PBC肝移植或死亡的临床获益》Gut,2020年8月 (4)
熊去氧胆酸是常用的治疗PBC的药物,但绝对临床获益没有测算过。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估用熊去氧胆酸治疗PBC的过程中,需要治疗多少例患者才能防止1例肝移植或死亡。研究纳入了3902例患者,平均随访时间为7.8年。
总的来说,熊去氧胆酸治疗5年,每治疗11人,可减少1例肝移植或死亡。分情况讨论,肝硬化患者中,5年内每治疗4人可减少1例肝移植或死亡;非肝硬化患者中为20人减少1例肝移植或死亡。5年内,碱性磷酸酶正常或轻度升高(<2ULN)的情况下,每治疗26人可以减少1例肝移植或死亡;碱性磷酸酶中度升高(2~4ULN)的情况下,每治疗11人可以减少1例肝移植或死亡;碱性磷酸酶重度升高(>4ULN)的情况下,每治疗5人可以减少1例肝移植或死亡。
结论:熊去氧胆酸相对于肝移植或死亡的绝对临床效益虽然不同,但始终是高的;因此,推荐所有PBC患者立即开始熊去氧胆酸的治疗,并通过健康宣教刺激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荟萃分析:奥贝胆酸与熊去氧胆酸联合治疗对熊去氧胆酸反应不好的PBC》Europe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2020年7月 (5)
奥贝胆酸是2016年FDA上市的一种半合成胆汁酸,用于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本研究荟萃分析了,单用熊去氧胆酸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中联用奥贝胆酸的疗效。研究纳入2个符合标准的临床实验、222例患者。
结果显示联合用药可进一步降低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谷氨酰转肽酶和C反应蛋白;但在改善碱性磷酸酶、血清总胆红素上无显著差异。
结论:联合用药有一定优势,但有效性仍需要高质量的RCT研究求证。
Barrett食管
Barrett食管是指化生柱状上皮取代正常情况下远端食管内覆盖的复层鳞状上皮,化生柱状上皮同时具有胃上皮和肠上皮的特征。Barrett食管由慢性胃食管返流病导致,容易发展为食管腺癌。危险因素包括:食管裂孔疝、年龄≥50岁、男性、慢性胃食管返流病、白种人、向心性肥胖、吸烟,以及一级亲属有Barrett食管或食管腺癌史。
Barrett食管筛查主要通过上消化道内镜联合活检。Barrett食管的治疗主要包括抑酸治疗和内镜治疗。大部分高级别异型增生或黏膜内癌患者都应该接受内镜根除治疗。
《随机对照研究:细胞海绵-三叶因子3用于鉴别Barrett食管》Lancet,2020年8月(6)
剑桥大学研究人员研制的新型的、不依赖于内镜检查的、用于诊断Barrett食管的细胞海绵-三叶因子3(Cytosponge- TFF3)检测法,形似小药丸,患者吞咽后达到胃部会膨胀为小海绵,迅速拉出后收集到的食管细胞可用于检测TFF3。这项研究旨在评估在正在治疗胃食管反流的患者中,TFF3检测法是否能提高Barrett食管的检出率。这项多中心、实用、随机对照试验招募了≥50岁、因胃食管反流服用抑酸剂超过6个月的、在过去5年内未接受内镜检查的患者共13514人,被随机分配到常规诊疗组(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接受内镜检查)或TFF3检测组(TFF3检测阳性时接受内镜检查)。
随机化后,TFF3检测组中有3%结果阳性,然后接受了内镜检查。随访12个月后,TFF3检测组中2%和常规诊疗组中0.2%的患者被诊断为Barrett食管(p<0·0001)。在TFF3检测组中,9人被诊断为发育不良性Barrett食管,4人被诊断为食管-胃交界区早癌;但在常规诊疗组为0。
结论:在胃食管反流患者中,TFF3检测法可以提高Barrett食管的检出率,还可以诊断出发育不良Barrett食管和早癌;但也存在假阳性结果并导致不必要的内镜检查。
《用电子鼻装置通过呼气检测Barrett’s食管》Gut,2020年7月 (7)
这项对402名患者进行的概念验证阶段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电子鼻装置分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开发并交叉验证了Barrett’s食管的预测模型。目前这种电子鼻诊断Barrett’s食管的敏感性91%、特异度74%,且诊断结果的准确性与是否使用质子泵抑制剂、是否存在裂孔疝和是否有反流无关。
结论:该技术可提供一种有效、耐受性好、敏感、特异的筛查方法,筛选高危人群行进一步的内镜检查。
《前瞻性研究:关于中国人食管癌前病变和此后8.5年的癌症风险的》,Am J Gastroenterology,2020年7月 (8)
这是一项由上海瑞金医院组织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对2005-2009年、3个食道癌高发地区、年龄40-69岁之间的21,111名患者进行内镜筛查,并随访至2016年。
在平均8.5年的随访中,我们发现143例新的食道鳞状细胞癌和62例死亡。鳞状细胞异型增生分级升高与鳞状细胞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有关。严重异常增生/原位癌、中度异常增生和轻度异常增生的癌症累积发病率分别为15.5%、4.5%和1.4%。50-69岁癌症发病率比40-49岁高3.1倍,男性比女性高2.4倍。
结论:本研究认为严重异型增生和原位癌需要临床治疗,中国高发地区首次筛查食管癌可推迟至50岁,对于轻中度异常增生的复查间隔可延长至5年和3年。
胰腺炎
急性胰腺炎是胰腺急性炎症过程,以腹痛和血胰酶水平升高为临床特征的疾病。常见的诱发因素包括胆石症、酒精、高脂血症、基因突变。急性胰腺炎可分为急性间质水肿型胰腺炎和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治疗包括液体复苏、疼痛控制和营养支持,必要时给予抗感染、坏死组织清除术等。
急性胰腺炎反复发作可能逐渐形成慢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是一种胰腺进行性、炎性改变的综合征,可导致胰腺结构永久性损害,从而引起外分泌和内分泌功能不全。治疗主要是针对疼痛和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口服药物无法缓解的重度疼痛患者,可以考虑采用腹腔神经阻滞、内镜下梗阻胰管减压、体外震波碎石、放疗、手术切除疑似胰腺癌。
《APEC研究:急诊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合并括约肌切开术与保守治疗对严重急性胆源性胰腺炎的疗效比较》Lancet,2020年7月 (9)
这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中,纳入严重的、无胆管炎的胆石性胰腺炎患者共232例,随机分配到急诊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联合括约肌切开术组、或保守治疗组。
6个月内死亡和主要并发症,在急诊手术组和保守治疗组分别为38%和44%(p = 0·37),胆管炎的发生率分别为2%和10%(p=0.010)。其他主要终点的单个组成部分没有显著差异。两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似。
结论:与保守治疗相比,急诊手术并没有降低主要并发症的或死亡率。
《ESCAPE研究:比较早期手术与内镜检查后再手术对慢性胰腺炎患者疼痛的影响》JAMA,2020年1月 (10)
这项无盲、多中心、随机、临床优势试验中,共纳入88例慢性胰腺炎伴严重疼痛的患者,随机分入早期手术组(6周内进行胰管引流手术)和内镜检查组(必要时碎石或手术),随访18个月。
早期手术组中,患者的Izbicki疼痛评分低于内镜检查后手术组(37分 vs 49分,P =0.02)。在随访结束时,早期手术组58%的患者疼痛完全或部分缓解,内镜检查组组为39%(P =0.10)。早期手术组的干预总次数较低(1次 vs 3次,P<0.001)。治疗并发症、死亡率、住院率、胰腺功能和生活质量在两组间没有显著差异。
结论:18个月后,慢性胰腺炎患者接受早期手术,接受的干预次数较少、疼痛控制效果更好。
《回顾性研究:高危患者中,消炎痛栓预防ERCP后胰腺炎时代的实践模式》Am J Gastroenterology,2020年6月 (11)
2012年曾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试验,证实了消炎痛栓预防高危患者接受内窥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后胰腺炎。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对这项研究的推广应用进行了调查,并且评估胰管支架使用的并发趋势,并估计这些变化对高危人群术后胰腺炎的影响。研究收集了26个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电子健康档案。
10年间高危患者中进行了26820次ERCP,术后胰腺炎发生率为8.6%,且2012年到2018年这个比例没有下降。从2012年开始,虽然消炎痛栓的使用量直线上升,但直至2018年使用率仍在50%以下。随着消炎痛栓使用的增加,2013-2014年胰管支架使用率急剧下降(40.7%-8.5%),最低只有3.0%。
结论:尽管消炎痛栓成本低、易获得,而且I级证据证明它可以降低高危患者的ERCP后胰腺炎的风险;但在ERCP期间,直肠消炎痛栓的使用率仍较低。
肠神经系统
《综述:肠神经系统》Nature Review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2020年6月 (12)
胃肠道是唯一具有独立神经系统的内脏器官,被称为肠神经系统(ENS)。这篇文章综述了肠神经系统神经元如何协调感觉和运动功能的。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
(1)在脊椎动物中,ENS对维持胃肠功能的非常重要。
(2)肠道能够将机械性或化学性刺激转换成神经活动,推动胃肠道运动。
(3)肌肉感知因素对膨胀诱发的结肠蠕动至关重要,这种感知功能是位于胃肠肌丛和/或圆形肌中,而不需要粘膜或粘膜下丛的参与。
(4)有证据表明,粘膜细胞(如肠内分泌细胞)释放的物质可以调节ENS的活性,但是像血清素这样的介质的释放对于膨胀诱发的蠕动、或结肠迁移运动并不是必要条件。
(5)外源性脊髓传入神经与内源性感觉神经虽然存在于在肠道的同一区域,但他们的激活机制是有本质差异的。
(6)目前光遗传技术的改进和应用,允许科学家能够刺激特定的神经化学神经元,以阐明其功能。
这篇综述还重点介绍了ENS中内源性感觉神经元如何检测和响应感觉刺激,以及这些机制与内脏中的外源性感觉神经末梢(内脏-大脑轴的神经系统)有何不同。
参考文献
1.Abou-Alfa GK, Sahai V, Hollebecque A, Vaccaro G, Melisi D, Al-Rajabi R, et al. Pemigatinib for previously treated,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phase 2 study. Lancet Oncol. 2020;21(5):671-84.
2.Abou-Alfa GK, Macarulla T, Javle MM, Kelley RK, Lubner SJ, Adeva J, et al. Ivosidenib in IDH1-mutant, chemotherapy-refractory cholangiocarcinoma (ClarIDHy):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study. The Lancet Oncology. 2020;21(6):796-807.
3.Murillo Perez CF, Harms MH, Lindor KD, van Buuren HR, Hirschfield GM, Corpechot C, et al. Goals of Treatment for Improved Survival in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Treatment Target Should Be Bilirubin Within the Normal Range and Normalization of Alkaline Phosphatase. Am J Gastroenterol. 2020;115(7):1066-74.
4.Harms MH, de Veer RC, Lammers WJ, Corpechot C, Thorburn D, Janssen HLA, et al. Number needed to treat with ursodeoxycholic acid therapy to prevent liver transplantation or death in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Gut. 2020;69(8):1502-9.
5.Li X, Liao M, Pan Q, Xie Q, Yang H, Peng Y, et al. Combination therapy of obeticholic acid and ursodeoxycholic acid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who respond incompletely to ursodeoxycholic acid: a systematic review. 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0.
6.Fitzgerald RC, di Pietro M, O'Donovan M, Maroni R, Muldrew B, Debiram-Beecham I, et al. Cytosponge-trefoil factor 3 versus usual care to identify Barrett's oesophagus in a primary care setting: a multicentre, pragmatic,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20;396(10247):333-44.
7.Peters Y, Schrauwen RWM, Tan AC, Bogers SK, de Jong B, Siersema PD. Detection of Barrett's oesophagus through exhaled breath using an electronic nose device. Gut. 2020;69(7):1169-72.
8.Wei WQ, Hao CQ, Guan CT, Song GH, Wang M, Zhao DL, et al. Esophageal Histological Precursor Lesions and Subsequent 8.5-Year Cancer Risk in a Population-Based Prospective Study in China. Am J Gastroenterol. 2020;115(7):1036-44.
9.Schepers NJ, Hallensleben NDL, Besselink MG, Anten MGF, Bollen TL, da Costa DW, et al. Urgent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with sphincterotomy versus conservative treatment in predicted severe acute gallstone pancreatitis (APEC):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20;396(10245):167-76.
10.Issa Y, Kempeneers MA, Bruno MJ, Fockens P, Poley JW, Ahmed Ali U, et al. Effect of Early Surgery vs Endoscopy-First Approach on Pai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ancreatitis: The ESCAPE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2020;323(3):237-47.
11.Smith ZL, Elmunzer BJ, Cooper GS, Chak A. Real-World Practice Patterns in the Era of Rectal Indomethacin for Prophylaxis Against Post-ERCP Pancreatitis in a High-Risk Cohort. Am J Gastroenterol. 2020;115(6):934-40.
12.Spencer NJ, Hu H. Enteric nervous system: sensory transduction, neural circuits and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0;17(6):338-51.
 View all episodes
View all episodes


 By 听友156612348
By 听友156612348




5
11 ratings

FDA 连续批准2个治疗胆管癌的靶向药
Lancet 细胞海绵-三叶因子3监测法筛查Barrett食管
Nature 胃肠道也有独立的神经系统
培米加替尼(Pemigatinib)
约20%的肝内胆管癌患者存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2融合基因突变,培米加替尼(Pemigatinib)是一种选择性FGFR抑制剂。2020年4月,FDA批准培米加替尼治疗复发性的FGFR2基因融合或重排的局部晚期胆管癌。
《FIGHT-202研究:培米加替尼治疗晚期胆管癌的临床研究》Lancet Oncology,2020年5月 (1)
这个多中心、非盲、单臂、2阶段研究纳入FGFR2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胆管癌患者、其他FGF/FGFR基因突变的患者、和没有FGF/FGFR基因突变的患者肱146人。所有入组患者均接受培米加替尼治疗直到疾病进展、不可接受的毒性、撤回同意或医生决定。
中位随访17·8个月,FGFR2融合或重排患者中35·5%达到客观缓解(其中3例完全缓解,35人部分缓解)。高磷酸盐血症是最常见的不良事件,49%的患者在研究期间死亡,最常见的原因是疾病进展,与治疗无关。
结论:培米加替尼在以前治疗过的发生FGFR2融合或重排的胆管癌患者中均有一定疗效。
艾伏尼布(ivosidenib)
基因组分析表明,胆管癌中有13%的患者存在IDH1基因突变,艾伏尼布(ivosidenib)是一种新型的小分子靶向异柠檬酸脱氢酶1(IDH1)抑制剂。艾伏尼布2018年被FDA批准用于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一线治疗,2020年4月批准用于胆管癌靶向治疗药物。
《ClarIDHy研究:针对胆管癌异柠檬酸脱氢酶1(IDH-1)突变的新型靶向疗法的3期临床研究》Lancet Oncology,2020年8月 (2)
胆管癌是一种对化疗敏感的癌症。尽管吉西他滨联合顺铂的一线化疗是标准治疗方案,但二线治疗却效果有限。这项国际性、双盲、安慰剂对照的、随机的、3期临床试验中,招募了185例携带IDH-1突变的胆管癌患者,其中大部分患者原发性肝内胆管癌(90%~95%)伴远处转移(92%~93%),随机接受艾伏尼布或安慰剂治疗。
中位随访6.9个月时,艾伏尼布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优于安慰剂组(2.7个月 vs 1.4个月,P<0.0001)。因为本试验允许安慰剂组患者发生进展后,跨组接受艾伏尼布治疗,因此艾伏尼布组和安慰剂组的中位总生存期相似。虽然艾伏尼布组只有2%的患者达到客观缓解,但51%达到疾病稳定。最常见的严重不良反应是腹水。
结论:艾伏尼布是一种靶向IDH-1突变的药物,可改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并使疾病稳定。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gnitis,PBC),也称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是一种慢性胆汁淤积性、自身免疫性肝病,可导致肝硬化。病理特征是T淋巴细胞攻击肝小叶内的小胆管,胆管上皮细胞收到持续攻击,导致胆管逐渐破坏、消失。临床表现包括黄疸、碱性磷酸酶升高、转氨酶升高、血脂异常、抗线粒体抗体(AMA)阳性95%、抗核抗体(ANA)阳性70%。PBC治疗有2个目标:(1)治疗慢性胆汁淤积引起的症状及并发症:包括症状性脂肪泻、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甲状腺功能减退、严重高脂血症、贫血、消化道出血、肝硬化等需分情况处理。(2)抑制肝小叶内小胆管的破坏:病因治疗并不很成功,获批准的治疗仅有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 acid,UDCA)和奥贝胆酸(obeticholic acid,OCA);尚存争议的疗法包括秋水仙碱、甲氨蝶呤。
《GLOBAL PBC研究:提高PBC患者生存率的治疗目标》Am J Gastroenterology,2020年7月 (3)
虽然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胆红素和碱性磷酸酶被广泛认为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但是治疗目标应该是多少,与生存率的关系如何依据不足。文章作者采用GLOBAL PBC研究中的欧洲和北美中心的长期随访数据。
胆红素≤0.6×ULN的患者10年生存率为91.3%,胆红素水平大于0.6×ULN时,肝移植或死亡的风险逐渐增加。碱性磷酸酶正常的患者10年生存率为93.2%,在1.0-1.67×ULN之间的患者10年生存率为86.1%。
结论:当胆红素水平≤0.6×ULN或碱性磷酸酶正常的时候,患者发生肝移植或死亡风险最低,这对治疗目标的制定有重要的意义。
《病例对照研究:熊去氧胆酸治疗预防PBC肝移植或死亡的临床获益》Gut,2020年8月 (4)
熊去氧胆酸是常用的治疗PBC的药物,但绝对临床获益没有测算过。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估用熊去氧胆酸治疗PBC的过程中,需要治疗多少例患者才能防止1例肝移植或死亡。研究纳入了3902例患者,平均随访时间为7.8年。
总的来说,熊去氧胆酸治疗5年,每治疗11人,可减少1例肝移植或死亡。分情况讨论,肝硬化患者中,5年内每治疗4人可减少1例肝移植或死亡;非肝硬化患者中为20人减少1例肝移植或死亡。5年内,碱性磷酸酶正常或轻度升高(<2ULN)的情况下,每治疗26人可以减少1例肝移植或死亡;碱性磷酸酶中度升高(2~4ULN)的情况下,每治疗11人可以减少1例肝移植或死亡;碱性磷酸酶重度升高(>4ULN)的情况下,每治疗5人可以减少1例肝移植或死亡。
结论:熊去氧胆酸相对于肝移植或死亡的绝对临床效益虽然不同,但始终是高的;因此,推荐所有PBC患者立即开始熊去氧胆酸的治疗,并通过健康宣教刺激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荟萃分析:奥贝胆酸与熊去氧胆酸联合治疗对熊去氧胆酸反应不好的PBC》Europe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2020年7月 (5)
奥贝胆酸是2016年FDA上市的一种半合成胆汁酸,用于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本研究荟萃分析了,单用熊去氧胆酸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中联用奥贝胆酸的疗效。研究纳入2个符合标准的临床实验、222例患者。
结果显示联合用药可进一步降低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谷氨酰转肽酶和C反应蛋白;但在改善碱性磷酸酶、血清总胆红素上无显著差异。
结论:联合用药有一定优势,但有效性仍需要高质量的RCT研究求证。
Barrett食管
Barrett食管是指化生柱状上皮取代正常情况下远端食管内覆盖的复层鳞状上皮,化生柱状上皮同时具有胃上皮和肠上皮的特征。Barrett食管由慢性胃食管返流病导致,容易发展为食管腺癌。危险因素包括:食管裂孔疝、年龄≥50岁、男性、慢性胃食管返流病、白种人、向心性肥胖、吸烟,以及一级亲属有Barrett食管或食管腺癌史。
Barrett食管筛查主要通过上消化道内镜联合活检。Barrett食管的治疗主要包括抑酸治疗和内镜治疗。大部分高级别异型增生或黏膜内癌患者都应该接受内镜根除治疗。
《随机对照研究:细胞海绵-三叶因子3用于鉴别Barrett食管》Lancet,2020年8月(6)
剑桥大学研究人员研制的新型的、不依赖于内镜检查的、用于诊断Barrett食管的细胞海绵-三叶因子3(Cytosponge- TFF3)检测法,形似小药丸,患者吞咽后达到胃部会膨胀为小海绵,迅速拉出后收集到的食管细胞可用于检测TFF3。这项研究旨在评估在正在治疗胃食管反流的患者中,TFF3检测法是否能提高Barrett食管的检出率。这项多中心、实用、随机对照试验招募了≥50岁、因胃食管反流服用抑酸剂超过6个月的、在过去5年内未接受内镜检查的患者共13514人,被随机分配到常规诊疗组(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接受内镜检查)或TFF3检测组(TFF3检测阳性时接受内镜检查)。
随机化后,TFF3检测组中有3%结果阳性,然后接受了内镜检查。随访12个月后,TFF3检测组中2%和常规诊疗组中0.2%的患者被诊断为Barrett食管(p<0·0001)。在TFF3检测组中,9人被诊断为发育不良性Barrett食管,4人被诊断为食管-胃交界区早癌;但在常规诊疗组为0。
结论:在胃食管反流患者中,TFF3检测法可以提高Barrett食管的检出率,还可以诊断出发育不良Barrett食管和早癌;但也存在假阳性结果并导致不必要的内镜检查。
《用电子鼻装置通过呼气检测Barrett’s食管》Gut,2020年7月 (7)
这项对402名患者进行的概念验证阶段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电子鼻装置分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开发并交叉验证了Barrett’s食管的预测模型。目前这种电子鼻诊断Barrett’s食管的敏感性91%、特异度74%,且诊断结果的准确性与是否使用质子泵抑制剂、是否存在裂孔疝和是否有反流无关。
结论:该技术可提供一种有效、耐受性好、敏感、特异的筛查方法,筛选高危人群行进一步的内镜检查。
《前瞻性研究:关于中国人食管癌前病变和此后8.5年的癌症风险的》,Am J Gastroenterology,2020年7月 (8)
这是一项由上海瑞金医院组织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对2005-2009年、3个食道癌高发地区、年龄40-69岁之间的21,111名患者进行内镜筛查,并随访至2016年。
在平均8.5年的随访中,我们发现143例新的食道鳞状细胞癌和62例死亡。鳞状细胞异型增生分级升高与鳞状细胞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有关。严重异常增生/原位癌、中度异常增生和轻度异常增生的癌症累积发病率分别为15.5%、4.5%和1.4%。50-69岁癌症发病率比40-49岁高3.1倍,男性比女性高2.4倍。
结论:本研究认为严重异型增生和原位癌需要临床治疗,中国高发地区首次筛查食管癌可推迟至50岁,对于轻中度异常增生的复查间隔可延长至5年和3年。
胰腺炎
急性胰腺炎是胰腺急性炎症过程,以腹痛和血胰酶水平升高为临床特征的疾病。常见的诱发因素包括胆石症、酒精、高脂血症、基因突变。急性胰腺炎可分为急性间质水肿型胰腺炎和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治疗包括液体复苏、疼痛控制和营养支持,必要时给予抗感染、坏死组织清除术等。
急性胰腺炎反复发作可能逐渐形成慢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是一种胰腺进行性、炎性改变的综合征,可导致胰腺结构永久性损害,从而引起外分泌和内分泌功能不全。治疗主要是针对疼痛和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口服药物无法缓解的重度疼痛患者,可以考虑采用腹腔神经阻滞、内镜下梗阻胰管减压、体外震波碎石、放疗、手术切除疑似胰腺癌。
《APEC研究:急诊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合并括约肌切开术与保守治疗对严重急性胆源性胰腺炎的疗效比较》Lancet,2020年7月 (9)
这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中,纳入严重的、无胆管炎的胆石性胰腺炎患者共232例,随机分配到急诊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联合括约肌切开术组、或保守治疗组。
6个月内死亡和主要并发症,在急诊手术组和保守治疗组分别为38%和44%(p = 0·37),胆管炎的发生率分别为2%和10%(p=0.010)。其他主要终点的单个组成部分没有显著差异。两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似。
结论:与保守治疗相比,急诊手术并没有降低主要并发症的或死亡率。
《ESCAPE研究:比较早期手术与内镜检查后再手术对慢性胰腺炎患者疼痛的影响》JAMA,2020年1月 (10)
这项无盲、多中心、随机、临床优势试验中,共纳入88例慢性胰腺炎伴严重疼痛的患者,随机分入早期手术组(6周内进行胰管引流手术)和内镜检查组(必要时碎石或手术),随访18个月。
早期手术组中,患者的Izbicki疼痛评分低于内镜检查后手术组(37分 vs 49分,P =0.02)。在随访结束时,早期手术组58%的患者疼痛完全或部分缓解,内镜检查组组为39%(P =0.10)。早期手术组的干预总次数较低(1次 vs 3次,P<0.001)。治疗并发症、死亡率、住院率、胰腺功能和生活质量在两组间没有显著差异。
结论:18个月后,慢性胰腺炎患者接受早期手术,接受的干预次数较少、疼痛控制效果更好。
《回顾性研究:高危患者中,消炎痛栓预防ERCP后胰腺炎时代的实践模式》Am J Gastroenterology,2020年6月 (11)
2012年曾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试验,证实了消炎痛栓预防高危患者接受内窥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后胰腺炎。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对这项研究的推广应用进行了调查,并且评估胰管支架使用的并发趋势,并估计这些变化对高危人群术后胰腺炎的影响。研究收集了26个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电子健康档案。
10年间高危患者中进行了26820次ERCP,术后胰腺炎发生率为8.6%,且2012年到2018年这个比例没有下降。从2012年开始,虽然消炎痛栓的使用量直线上升,但直至2018年使用率仍在50%以下。随着消炎痛栓使用的增加,2013-2014年胰管支架使用率急剧下降(40.7%-8.5%),最低只有3.0%。
结论:尽管消炎痛栓成本低、易获得,而且I级证据证明它可以降低高危患者的ERCP后胰腺炎的风险;但在ERCP期间,直肠消炎痛栓的使用率仍较低。
肠神经系统
《综述:肠神经系统》Nature Review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2020年6月 (12)
胃肠道是唯一具有独立神经系统的内脏器官,被称为肠神经系统(ENS)。这篇文章综述了肠神经系统神经元如何协调感觉和运动功能的。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
(1)在脊椎动物中,ENS对维持胃肠功能的非常重要。
(2)肠道能够将机械性或化学性刺激转换成神经活动,推动胃肠道运动。
(3)肌肉感知因素对膨胀诱发的结肠蠕动至关重要,这种感知功能是位于胃肠肌丛和/或圆形肌中,而不需要粘膜或粘膜下丛的参与。
(4)有证据表明,粘膜细胞(如肠内分泌细胞)释放的物质可以调节ENS的活性,但是像血清素这样的介质的释放对于膨胀诱发的蠕动、或结肠迁移运动并不是必要条件。
(5)外源性脊髓传入神经与内源性感觉神经虽然存在于在肠道的同一区域,但他们的激活机制是有本质差异的。
(6)目前光遗传技术的改进和应用,允许科学家能够刺激特定的神经化学神经元,以阐明其功能。
这篇综述还重点介绍了ENS中内源性感觉神经元如何检测和响应感觉刺激,以及这些机制与内脏中的外源性感觉神经末梢(内脏-大脑轴的神经系统)有何不同。
参考文献
1.Abou-Alfa GK, Sahai V, Hollebecque A, Vaccaro G, Melisi D, Al-Rajabi R, et al. Pemigatinib for previously treated,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phase 2 study. Lancet Oncol. 2020;21(5):671-84.
2.Abou-Alfa GK, Macarulla T, Javle MM, Kelley RK, Lubner SJ, Adeva J, et al. Ivosidenib in IDH1-mutant, chemotherapy-refractory cholangiocarcinoma (ClarIDHy):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study. The Lancet Oncology. 2020;21(6):796-807.
3.Murillo Perez CF, Harms MH, Lindor KD, van Buuren HR, Hirschfield GM, Corpechot C, et al. Goals of Treatment for Improved Survival in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Treatment Target Should Be Bilirubin Within the Normal Range and Normalization of Alkaline Phosphatase. Am J Gastroenterol. 2020;115(7):1066-74.
4.Harms MH, de Veer RC, Lammers WJ, Corpechot C, Thorburn D, Janssen HLA, et al. Number needed to treat with ursodeoxycholic acid therapy to prevent liver transplantation or death in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Gut. 2020;69(8):1502-9.
5.Li X, Liao M, Pan Q, Xie Q, Yang H, Peng Y, et al. Combination therapy of obeticholic acid and ursodeoxycholic acid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who respond incompletely to ursodeoxycholic acid: a systematic review. 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0.
6.Fitzgerald RC, di Pietro M, O'Donovan M, Maroni R, Muldrew B, Debiram-Beecham I, et al. Cytosponge-trefoil factor 3 versus usual care to identify Barrett's oesophagus in a primary care setting: a multicentre, pragmatic,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20;396(10247):333-44.
7.Peters Y, Schrauwen RWM, Tan AC, Bogers SK, de Jong B, Siersema PD. Detection of Barrett's oesophagus through exhaled breath using an electronic nose device. Gut. 2020;69(7):1169-72.
8.Wei WQ, Hao CQ, Guan CT, Song GH, Wang M, Zhao DL, et al. Esophageal Histological Precursor Lesions and Subsequent 8.5-Year Cancer Risk in a Population-Based Prospective Study in China. Am J Gastroenterol. 2020;115(7):1036-44.
9.Schepers NJ, Hallensleben NDL, Besselink MG, Anten MGF, Bollen TL, da Costa DW, et al. Urgent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with sphincterotomy versus conservative treatment in predicted severe acute gallstone pancreatitis (APEC):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20;396(10245):167-76.
10.Issa Y, Kempeneers MA, Bruno MJ, Fockens P, Poley JW, Ahmed Ali U, et al. Effect of Early Surgery vs Endoscopy-First Approach on Pai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ancreatitis: The ESCAPE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2020;323(3):237-47.
11.Smith ZL, Elmunzer BJ, Cooper GS, Chak A. Real-World Practice Patterns in the Era of Rectal Indomethacin for Prophylaxis Against Post-ERCP Pancreatitis in a High-Risk Cohort. Am J Gastroenterol. 2020;115(6):934-40.
12.Spencer NJ, Hu H. Enteric nervous system: sensory transduction, neural circuits and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0;17(6):338-51.

438 Listeners

431 Listeners

62 Listeners

369 Listeners

296 Listen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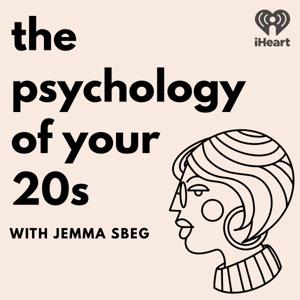
1,379 Listen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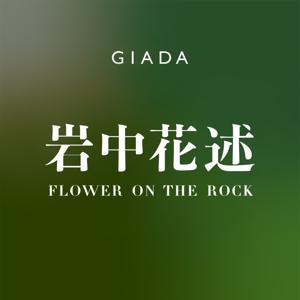
326 Listeners

163 Listeners

251 Listeners

286 Listeners

3 Liste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