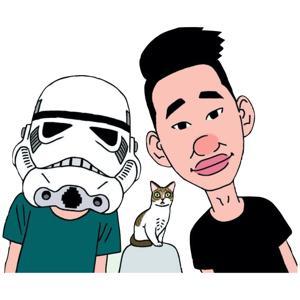高敏感人,即係點?
要回答呢個問題,最好就交畀《高敏感情緒自救手冊》嘅作者卡魯恩・霍爾(Karyn D. Hall)。佢係心理學家、辯證行為治療(DBT)治療師,休斯頓辯證行為療法中心主任,佢專長研究嘅,係高敏人——同大多數人相比,高敏人即係會更頻繁、更持久咁經歷強烈情感嘅人群。
而作者認為情緒高度敏感既係一種天賦,亦係一種負擔。因為高敏人好多時都係具有兩面性:
有啲人喺情緒嘅洪流中受益匪淺
有啲人就掙扎喺負面情緒中,難以自拔,好難留意到呢啲情緒背後嘅積極意義。
點解高敏人都係情緒高度敏感,但係會得到咁唔同嘅結果呢?
如果你係一個情緒敏感嘅人,咁你對他人嘅關心、狂喜嘅快樂、強烈嘅情感連繫,以及對大自然嘅熱愛,都會為你嘅人生增添目標感、意義同滿足感。但如果情緒一再將你吞噬,太大嘅負擔就可能令你唔會覺得高度敏感係一種天賦。學識管理情緒唔單止可以減少你嘅痛苦,仲可以幫你享受情緒帶嚟嘅更多恩賜。
管理情緒需要你承認同接受自己嘅情緒,用健康嘅方式應對唔舒服嘅感覺,並學會揀選合適嘅行為去管理情緒。
例如,當你覺得唔舒服時,糾結於需唔需要請人幫手照顧活潑好動嘅小朋友。結果你可能會瘋狂購物直至荷包扁晒,可能會暴飲暴食,又或者會對你心愛嘅人亂發脾氣。
我哋會一齊慢慢讀呢本書,每一個章節後面仲會有一啲練習題。當你讀到一啲對你有幫助嘅技能或者觀點嘅時候,記得我哋喺《最高學以致用法》當中所講嘅:要記錄呢一啲嘅觀點,然後將觀點確切咁樣輸出。
無論你嘅情緒係唔係高度敏感都好,希望你都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嘅情緒,得到一個更加輕鬆、愉悅嘅日常生活,而唔係被情緒操控。
我哋會假設你係一個情緒敏感嘅人嚟論述,如果你唔係情緒敏感,咁你就可以睇下情緒敏感嘅人係點樣諗嘢——因為你唔係,你家人、伴侶、朋友都可能係。
【高敏感情緒管理101-第一堂】認識高敏感之兩面——恩賜與詛咒
高敏人嘅基本特徵
愛好大自然
對他人情感高度敏感
過度包容或過度偏執
人際中嘅誤解
對拒絕敏感
情緒打工仔
選擇困難症
直覺強者(半盲)
創造力
強烈嘅正義感
不斷變化嘅身份
情緒點解咁敏感?
高敏人一定係心理障礙者?
小結
建議配合集數:
牛哥讀經(14)丨伯特蘭・羅素1丨如果想開心,不如「一天天的少關心自己」?羅素為你分析人類三大心病,揭露畏罪狂、自溺狂、自大狂嘅共通點丨傅雷譯,《幸福之路》,〈甚麼使人不快樂?〉
牛哥三個字|不快樂
為咗得出情緒敏感嘅積極意義,依家我哋就要了解一下情緒敏感嘅特點。
逢星期三夜晚九點直播
(如有字幕,字幕由ai生成,我無時間檢查,如有需要,自行取用)
閱讀材料:
《高敏感情緒自救手冊》
🐮 Follow IG:https://www.instagram.com/cowgortalk
🐂 加入讀物農莊,一齊閱讀,一齊討論!
https://www.patreon.com/cowgortalk
【文稿可於Patreon免費閱讀】
成為頻道會員並獲得福利: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6i3xQE-WhlKsu9l1cqzEQw/join
【聽Podcast】
🎧 Apple Podcast:https://podcasts.apple.com/podcast/id...
🎧 Spotify:https://open.spotify.com/show/0yFR7YK...
🎧 Google Podcast:https://bit.ly/3Cknf1m
🎧 KKBOX:https://bit.ly/3RneS9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