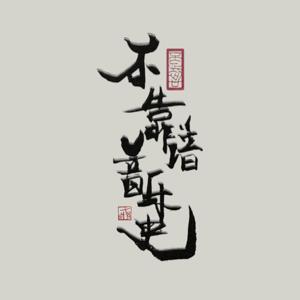乔治·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法国作曲家。1838年10月25日生于巴黎,1875年6月3日卒于同地。父亲是声乐教师,母亲出身于音乐世家。9岁从师A.-F.马蒙泰尔学钢琴。同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在P.-J.-G.齐默尔曼班学习。齐默尔曼多病,常由他的女婿C.古诺代课,1853年齐默尔曼去世,比才转入E.L.阿莱维作曲班。阿莱维很赏识他的才华。1869年比才与阿莱维的女儿结婚。
比才于12岁时开始创作,16岁时发表的两首歌曲,受古诺的影响。早期的钢琴曲有模仿F.李斯特和S.塔尔贝格的印记。比才的第1部独幕喜歌剧《医生之家》,受C.M.von韦伯和意大利歌剧的影响较深。17岁时写的《C大调交响曲》,形式严谨,旋律清新,色彩明快,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1856年比才参加J.奥芬巴赫主办的轻歌剧创作比赛,他所写的独幕歌剧《奇迹医生》获第1奖。1857年他作的康塔塔《克洛维和克洛提尔达》获罗马大奖。同年赴意大利留学。1858~1859年间他从事趣歌剧《唐普罗科皮奥》的创作,剧本和音乐都很象G.多尼采蒂的《唐帕斯夸尔》。其后有一段时间他在创作上产生了信念危机,尽管有许多创作计划,然而又一个个放弃。1859~1860年他着手写颂歌-交响曲《瓦斯科·德·加马》和喜歌剧《画家与爱情》。但都未能成功。
比才应征写了1部新歌剧《采珠人》(应征的条件是作曲者必须是没有一部歌剧上演过的获罗马大奖的青年作曲家),这是他的第1部重要的歌剧作品,于1863年首演。当时法国风行东方题材,《采珠人》是一部以锡兰为背景的爱情悲剧,虽然剧情脱不开三角恋爱的公式,但音乐富于生活气息,旋律丰富,至今仍是欧美各国经常演出的剧目。1865年比才完成另外1部歌剧《伊凡四世》,未能获得上演。1866年7月比才离开罗马回国,途中作北意大利旅行,在途中产生了交响音乐的构思,这就是1868年完成的标题组曲《罗马》。
1867年《珀斯城的美女》初次上演,它是比才唯一获得当时报刊好评的歌剧。但评论家若阿内斯·韦贝尔指出比才迎合部分听众的习惯,使创作沉溺于法国大歌剧的陈规旧套。比才接受了批评,在感谢信中发誓要摒弃华而不实的传统。
1868年比才的思想上再次出现10年前那样的精神危机,他写道:“我不论在做艺术家和做人方面都在脱胎换骨。”比才认识到社会必须改革,艺术必须与社会现实相联系,要创作完美而真实的新艺术作品。但是,比才的思想停留在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水平。他拒绝为拿破仑三世写歌功颂德的合唱,普法战争时他参加国民自卫军,他的理想是推翻第二帝国建立第三共和国。同时他又把巴黎工人的伟大起义看成是保皇党、教权派挑起来的,唯恐保皇党和教权派出来复辟君主制。他对巴黎公社持反对态度,哀叹“在白色狂暴和红色狂暴之间,正直的人们无容身之地”。
1872年上演的独幕歌剧《扎米雷》以埃及为背景,作者对东方题材的处理和风土人情的描绘都比《采珠人》前进了一步。比才采用了真正的阿拉伯旋律,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艺术加工,音乐对女主人公的形象刻划得细致入微,和声的运用新颖大胆。比才确信他在《扎米雷》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同年,比才应邀为法国文学家L.都德的话剧《阿莱城姑娘》写配乐。由于条件的限制,只允许他用26人的小乐队。这不仅没有束缚住他的手脚,反而促使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创作了这首至今仍在各国演出的名曲。《阿莱城姑娘》描写一个农村青年本来可以和心爱的姑娘维尔塔成家立业,安分守己地过一辈子,但是由于他迷恋放荡的阿莱城姑娘不能自拔而自杀。比才以鲜明的色彩描写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农村生活,成功地烘托出剧中主人公的悲惨结局,加强了戏剧的感染力量。比才特别显示了他在配器上的清新风格。他模拟钟声、铃声以及各种民间乐器的音响,运用人的闭口哼唱,使音乐独具风格。他以萨克斯管吹奏的旋律,表现痴呆少年的天真无邪;以弦乐小柔板表现年轻时曾相恋的老农和老妪重逢时的心情。话剧的演出并未获得成功,音乐却被改编为两套管弦乐组曲而流传下来,第1套是比才自己选编的,第2套是比才的朋友E.吉罗在他死后选编的。
歌剧《卡门》是比才的创作顶峰,剧情取材于P.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比才把社会底层人物──烟草女工和士兵推上了法国歌剧舞台,音乐与剧情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丰富的不同性格的旋律展现了五彩缤纷的生活画卷,刻划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在《卡门》中突破了法国喜歌剧的格局,力求体现现实主义原则。在音乐方面比才强调了剧情发展的对比和力度,写得生动、灵活、富于光彩,虽然只采用了3个西班牙民歌的曲调,却充分体现了西班牙的民族风格。群众场面在歌剧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群众热爱生活的喜气洋洋的场面,代替了原作中的阴森沉郁的气氛,尤其是最后一场,群众的欢乐和个人的悲剧形成强烈的对比,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戏剧效果。《卡门》的初演遭到失败,这使比才受到很大打击。3个月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比才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作曲家。在他的歌剧音乐中,把浓郁的民族色彩,动人心弦的戏剧矛盾冲突,个性鲜明的音乐语言,富有表现力的交响发展,以及法国喜歌剧传统的表现手法熔于一炉,这使他的歌剧艺术成为19世纪法国歌剧的最高成就。《卡门》成为世界各国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