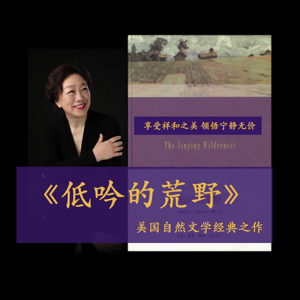就在十年前,鲍勃回到家里,要体验仲冬时节明尼苏—奎蒂科边界乡野的感觉。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再度与我同坐在一个黑色小屋里,观望着不停旋转的诱饵以及冰层下面的景色。他想拥有时光来打发漫漫的思绪,来听着外面的雪花轻轻地打在薄薄的焦油纸墙上的声音。他想拥有他曾经体验过的那种美好的感觉:滑了一整天雪之后,享受安顿下来的夜晚,或许还能品尝到从北方冰冷的湖水中刚捕捞上来的鲜鱼。
于是,在一月的一个早晨,尽管气温是零下二十摄氏度,我们照样出发,前往我们过去常去的地方。当我们在瀑布湖下游的水域中穿越行进时,滑雪用具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举目望去,路尽头的小城温顿,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太阳的虹光照亮了地平线。天气太冷,不能慢行。我们奋力撑着滑雪杖,滑雪板在干雪上发出嘶嘶的响声。只有我们在野外出行,只有我们傻呵呵地在完全没必要外出的情况下到野外来。然而,湖面上有鹿刚跑过的痕迹,而且,在通往锡达的陆路上有兔子、黄鼠狼和鼷鼠的足迹。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由焦油纸搭建的小屋,它位于一条狭长岬角尽头的水域。一位朋友几周前搭好了这个小屋,并告诉我们渔叉及木制诱饵的贮藏处。至于使用小屋的费用,我们给他带条鱼就行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得捉两条鱼。我们推走门前的积雪,在小炉子里点燃了火,从堆积物中翻腾出了渔叉及诱饵。
凿洞要挖出六英寸厚的冰。我们给咖啡壶里加满了水,关上门,然后坐下来等候。门外狂风呼啸,但小屋里却舒适温暖。起初,除了绿色的半透明的湖水之外,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们的视觉渐渐地清晰,可以看得越来越深,最终看到了湖底。光线穿透了冰雪,在湖底闪烁。
在我们的视野里有几块泛白的岩石、几个贝壳,那是此景重要的标志物。不久,大叶藻和毛茸茸的狐尾藻呈现于灰暗朦胧之中,在狭窄水道的微波中缓缓地摇曳。岩石和贝壳渐渐地熟悉起来,仿佛我们观望了它们许久,那一簇簇摇曳的水草也如同草地上的树丛一样引人注目。在一个角落里,有只蛤蜊,它移动时留在沙子上的痕迹明显而清晰。一束阳光斜射在我们的猎区,在闪闪发光的冰棱柱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舞台已搭好,只待好戏上演。此情此景值得我们冒着严寒艰难出行,补偿了我们几周来的苦苦等待;这是一种由荒凉的美丽和凝固所构成的景色,非任何精心设计的布景所能成就。
渔叉很随意地靠在冰层的内沿,它的把手是松开的,随时可以抓住,一根绳子将它固定在鲍勃手腕上。偶尔,他会移动渔叉的叉角,以免它在V形的凹口中插得太深;他会轻轻地扭转它,这样当大好时机到来时,便不会有阻力,不必费劲猛拉,掷渔叉时不会有任何障碍。当时机来临时,渔叉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袭击。
我负责摆弄诱饵,那是一个六英寸长的淡水鲦鱼模型,用闪亮的锡填上了鱼鳍和鱼尾。模型是由一块松木削成,以铅来增重。它被系在一条绳子的绳头。鱼尾是固定的,这样我的手一动,这诱饵便在冰洞里拼命地绕着漂亮的圈子。
咖啡开始轻轻地冒泡,我们脱了夹克,摘掉手套。屋外,温度依然接近零下二十摄氏度,如鲍勃所期望的那样,瑞雪低吟。忙碌了一小时之后,我们开始放松,低声细语地谈起了许多事情。一间垂钓小屋是个很好的去处——它不是为了谈那些宏图大论,而是悠然地闲聊,谈当地的政治活动、街谈巷议。我们的所见所闻纷纷而至,所谈的都是些不费吹灰之力的想法,简洁的思想如同呼吸般地轻松自如。这里可不是阐述那些高深信仰的地方,此类信念需要广阔的空间来滋长和扩展。况且,我们必须为了下面那银光闪烁的瞬间保存精力,因为那一瞬间将使得这世上的其他任何事物都黯然失色。
“能捉到一条北梭鱼做晚饭就好了。”我说。
“那就好了。”鲍勃回应说。
“我们要在它冻结前把它收拾干净,”我说, “这样回家就省事了。”
“看见那只蛤喇了吗?”鲍勃说, “它在朝着冰洞外面爬呢。趁着有时间,赶紧让开路。”
“早上看到的那些鹿脚印像是它们被追赶着似的。那一跳有二十英尺。”
“它们是往南岸的雪松林跑呢,真是在急着赶路。”
这种漫无边际的闲谈持续着,过了一阵子竟无话可说了,我们陷入了沉默,只是坐在那里,盯着冰洞,望着那个小木鱼有节奏地在水里绕圈子,来来回回,周而复始,它那金属的鱼鳍在光中闪烁。过了一会儿,我们的目光与湖底交融,从而开始感到仿佛我们成为身下世界的一部分,成为纯净的沙子、白色的岩石和摇曳的藻草的一部分。我们与湖底处处参差不齐的景物亲密无间,流动的波纹、每一片飘动的草叶,冰洞边缘鼓动的气泡,甚至还有外面浮云的倒影。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感观完全与地下那蓝绿色的世界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