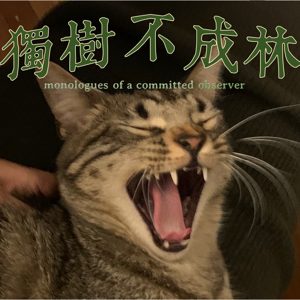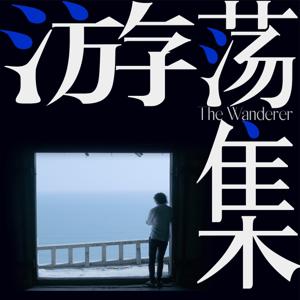收听提示
1.我们的教育,鼓励孩子去体验去追问吗?
2.城市的孩子和乡村的孩子之间,有区别吗?
3.乡村学校如何开展性教育?
本期嘉宾
梁文道
“看理想”策划人,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主讲人。
王世民
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新镇小学校长。他筹措资金办起陕西省第一所公办寄宿制小学,关注国外教育,曾在美国农村当“影子校长”。
正文
周轶君: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上集话题。上集我们说到印度人就是近看好像一群蜜蜂在乱飞,但隔远一点再看,就会发现这群蜜蜂正在缓慢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梁文道:印度的具体环境差异很大,其实很像中国。因为它也是个大国,人口那么多,每个邦,就我们平常讲的省都不一样,条件环境都不一样。所以它变成所有的全国性的系统并不是那么的能够统一起来。
比如说教育其实每个地方都不一样,资源也不一样,很难照顾个人需求,所以它需要很多个体做一些有创意的东西,就像你片子里面一样,其实印度整体教育它的义务教育是相对而言不算太发达的,其实是不好的,它是靠很多个体在努力。
周轶君:他甚至到了像您刚才说就吃午餐,学校要提供免费午餐,但不是像芬兰的那种免费午餐,他提供午餐是吸引学生来上课,因为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干嘛要上学,上学改变不了的命运。
梁文道:很悲惨的就还是有这种观念,不过印度现在之所以有潜力,人家觉得这几年它还是有潜力,就因为文盲的数字在不断下降,小学普及率在不断地上升,甚至中学普及率不断在上升,小学好像一般是读5年,然后中学就是6年级到12年级初中加高中,那它正在不断地在改变,所以还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这个国家,但我想问你一个东西,就是印度的这种个体的实验它能发生是它的国家政策,对这些东西怎么看呢?
周轶君:我觉得宽容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是很多时候他们都说你都要去尝试,这个空间都是自己去尝试,而且在教育这个环境下面的话,相对来说它做出来的努力还是比较得到认可的。
梁文道:所以你看我回到中国的情况,我觉得我们不要对自己的自我认知发生错误,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农村人口是他的收入平均其实是并不高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怎么样去做乡村教育。
比如说像王校长你做这个事情,其实你觉得我刚刚听你这么讲,我觉得你好像有一个挺大的空间给你,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或者整个体系是不是有像这种机会,也像印度一样,容许很多个别的实验跟创新,比如让你这么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王世民:现在说的乡村教育,首先这里边有很多不好的因素,比如说教学质量不好等等,很多方面的不好的一些想法,但是我在想乡村学校,特别乡村的教育,它是有它很多的城市学校不具备的一点,比如说空间,有足够的空间那么你很多的课堂,就能够施展开。
比如说小学的孩子人民币的认识,我在学校里我一直质问老师,我说这个课为什么要放在课堂里面去上?为什么不把它放到超市,跟超市老板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他当收银员的,他有买东西的,还有算账的,我说这不是很好的数学课堂吗。
另外一个就是老师也有时间,很多学校就是现在班很小,二三十,甚至有的学校现在就是一个班十几个孩子,二十个孩子,美国我去的好多学校都是18个22个。我就觉得小班,孩子的个性老师能关注到,如果他哪一方面需要老师去辅导,更重要就是老师有时间,比如说这对教育这块的研究,有这个平台,有学校,还有孩子。
周轶君:他就住在学校里面。
王世民:他很容易出成果,所以我在杭州师大,给师范生做那个职业生涯,十几分钟讲座,我说师范生比如说你有规划,我要是五年我要达到什么程度,十年要达到什么程度,我说你最好去乡村去。
因为城市你在那打拼十年,你可能在那个学校里边在那个地区,因为优秀的人才很多了,你相反你到乡村去,可能突然间你的位置、你这个人就很重要了。
梁文道:而且空间比较大,这个空间大,是不是指的同时是我们制度上面给乡村学校的自主实验的空间也比较大。
王世民:从国家这一块对教育上这块整个的设计方面就是就是知识的学习还很多,就是让孩子要去体验的,特别是在小的时候,要通过他们去体验,亲身去体验去发现问题,能够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后他能不能有新的追问?如果课堂能这样长期这样去做的话,我想那么这个孩子可能高中以后大学毕业以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就是原创的一些思想。
周轶君: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国家的教学大纲里面是有的,是孩子去体验去追问,但是在城市里面我们不太能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大家赶着要那个分数。
王世民:空间时间这块可能就不太允许,但是我在想可能这块还是很看好乡村的孩子,可能他们长大以后,这块让他们去能去体验能去发现问题,让他们自主去学习的话,当他就是走到工作岗位,走上社会以后,他可能就是说要给再创新,在很多方面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周轶君:这个听上去很像就是印度电影《起跑线》结尾的时候,那一个中产家庭最后把孩子送去了一个比较普通的公立学校,您这个介绍完以后,我估计很多家长都想要不把孩子送乡下也挺好的。
同样的那个电影你也看了,起跑线那个片子,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共鸣,很多观众都看这个片子,因为中国和印度一样,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特别快,当中很多人的阶层都变了,我当中也特别采访到有一个爸爸就是自己从乡村出来做企业高管,他认为就是说教育对于印度人来说也是唯一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它不仅仅是改变说阶层经济的面貌,对于它的种姓制度也是一样,就说到到了大学里面,他说就不太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了,就不太去看这个东西了。那么您觉得比如说在中国,您觉得乡村的孩子,教育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途径吗?
王世民:其实我觉得吃穿生活水准城市城乡差距在缩小。特别是乡村的孩子这块教育其实要培养他们什么意识呢,虽然是生在乡村在偏远的地方,作为学校老师校长一定要让孩子从小视野要开阔,从大的方面去讲,就是一个地方的责任对家乡的责任。
另一方面就是对国家的责任,乡村的孩子他们能够这样去想,我觉得他们现在所谓说的城市孩子乡村孩子,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梁文道:所以你不觉得有这个区别。
王世民:我不觉得有这个区别。其实这块我还一直在坚守一个观点,就是乡村的教育这块有一个责任,就是孩子不管他学得怎么好,他走得多远,就是要有乡村情怀,能够守得住家乡。那就是说你学什么专业技术,哪个学科,你是什么学历,最终我还是想让这些孩子将来能够建设乡村。
梁文道: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全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一种乡村的空洞化现象,比如说日本就非常严重,大家都往大城市去。那么过去几十年我们高速城镇化其实也是乡村在空洞化,所以说有一阵子留守儿童不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吗?
整个村子里面就只剩下老人跟小孩了。但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整个乡村会凋敝的,那么必须要找到一种重新振作乡村的方法,那我觉得中国在这一点上跟印度是很不一样的。在中国我们说改变一个人,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不必然像印度那样子,必须要逃离乡村才能改变命运。
我觉得这点上中国比印度公平,印度这个国家虽然说宪法上说的是不能够再有种姓制度,但实质上我们都晓得,日常生活种姓的这个观念很强烈。
周轶君:对,它强烈到,就是包括我当中那个作为取代保险存在的看管员,一开始他都不肯告诉我们他姓什么,不让我们知道。然后到后来不是你去机场,因为他的机票上你不写姓也不行,才给我们看。后来我们偷偷查了一下,他的姓其实是洗衣工,就是等于是贱民阶层,所以他都不让我们看这个姓。
梁文道:所以你看很多农村的人,就特别印度乡村地区,是种姓制度非常强大的。所以在乡村的小孩子他会觉得我要逃离,或者很多大人会觉得他怎么样逃离这种束缚或者不平等的状态,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城市。
所以为什么印度的城市有那么多的大型的平民窟,其实那个贫民窟你看到很多人是他在追求更平等的生活,他必须到城市,但他负担不起城市的生活,就留在那。我觉得中国好在还没有这个种姓问题,留在乡村就只是一个经济距离的问题而已。
王世民:我在想咱们国家现在乡村这一块,比如说现在的交通条件、医疗条件、教育,你可能现在看到在乡村这一块,可能很多都很好的建筑就是学校。房子盖得很好,设备设施也很到位。但是现在为什么一些家长愿意把孩子放在城里边去,就哪怕在城市里边住的也不好,毕竟师资还是不一样,(农村)教学质量可能就是差一点。
周轶君:城乡差距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很多自然环境这些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的。您在学校里的孩子,他们会问这些问题吗?
王世民:这块他们挺逗的,我在现在这个学校已经六年了,他们有时候问的问题,比如说他六年级毕业了,我说毕业了你给校长说一句话。他说校长你要好好去锻炼锻炼你的讲话。
我就觉得虽然说这句话我心里感受不太好,但是我就想,他能这样我很高兴,他能这样发现问题,他敢于去跟你说这个话,他肯定将来比我更强大。当然孩子这块我觉得有些方面也是,价值观是引导的问题。还有比如说现在家长讲“好好读书,读个好学校,将来找个好工作,有个好生活”。
我觉得家长可以这样去讲,但是从教育工作者,就是老师、校长这个层面,还是要少给孩子去讲这些问题,其实还是讲一些责任,一些担当,相反他们可能将来成长的更好。
周轶君:我问一个跟我们刚才聊得不是特别相关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印度不是专门拍了一些针对女孩子的(内容),她们会有一些使用卫生巾等等生理的教育,那在中国其实我们也在强调这种,比如说性教育这些东西要不要比较早的时候开始,甚至于比如说在乡村也好,在城市也好,就是孩子怎么保护自己等等。
那其实在这个方面,您觉得咱们是一个会专门拿出来讲的话题吗?还是我们是避而不谈的比较多一些?生理上怎么保护自己?
王世民:这一块在学校现在也是避不开的一个话题,虽然说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这个不是课堂,但是我们当校长,我们当老师,第一个就是要保护好孩子。我们还是跟我们西安市妇女联合会从2015年定期在每个学期有这方面的课程,专门对女孩子这块,她们生理、性别这方面的课程。
当然一个学期也不会很多,一个孩子可能一个学期也就上两节课,就是让他们懂得这个方面怎样自我保护,可能因为家长他好像也没有时间给娃去讲这些问题。
周轶君:大家甚至有些回避这些东西。
王世民:但是我刚才说的六年级孩子这块,比如说他第二个学期就比较难管,比如男女孩这块,比较喜欢亲近的问题。
梁文道:怎么办呢?
王世民:第二个学期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一块,对孩子视野的一些引导。
周轶君:比如呢?
王世民:比如我们学期开始给他们有一堂课就是给他们讲这块,比如人生,你长大以后的理想,你对自己有什么规划,主要就是把他们除了学习之外的那方面给他们能分散一下。周轶君:就是说不要想这些事儿,还是有更远大的理想。
梁文道:还不到时候。
王世民:另外一个就是开展很多活动。
周轶君:体育活动?
王世民:就是体育活动,艺术这一块。所以他的注意力转移了,你不能老去劝他。
周轶君:做一个高尚的人要摆脱的低级趣味。可是我觉得咱们还是真的没有这个方面的教育,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拿来用的东西,我们没有一个教材真正的跟孩子讲这个性教育,我反而在国外在欧洲看到他们有一些童书,很早他就会画出来这些,非常明确地告诉孩子,他们觉得可能越早知道,反而有这个透明度,孩子就不一定真的老是会去关注。
一开始其实我自己拍摄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大家对这个话题真的有这么大的需求,后来我收到了很多观众的反馈,都问这本书哪里可以买到,因为它的中文版据说马上要出了,然后很多的家长都给我留言说哪里可以有。因为大家对这个事情,虽然可以解释给孩子,可能不像在印度,他们问说哪个妈妈跟你讲过,只有一个孩子的妈妈讲过。
中国可能妈妈会说,但是你要解释的那么清楚,还有一本动画书给你讲可能是没有的,没有这种帮助她们去解释的材料。
王世民:这个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搞成一个我们的校本教材。
周轶君:这太有意思了,就是说您会专门做一个校本教材。
王世民:这个校本教材我是怎么去做,做好以后就是先发给孩子家长,慢慢有一个过程,突然间在学校里边可能有争议。
梁文道:对,我觉得在中国必须从家长开始。
王世民:我们给他们开家校联谊会的时候给家长去讲。
梁文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
周轶君:从王校长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作为一个教育者,当他自己觉得有思考的时候,他想去找答案的时候,他无论在美国还是看印度还是看哪里,他都会学到非常具体的方法,他有想法,然后他有办法。
而且拍印度还有个原因是,大家经常说到中国的任何问题就是我们人多,那印度有13亿人口。播出来的时候就特别逗,我看弹幕有一个观众就说,不是说印度不是有1亿人口吗?他说只有1亿。然后旁边有别的观众就回应说那是清朝的事情了。意思是说大家要更新我们对这些周边世界的认知,所以你具体看人家好不好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具体我们自己能拿来什么。
梁文道: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国在盯教育的时候老盯北欧,那其实我坦白讲,我觉得北欧当然很多方面很理想,但有时候可比性并不大,差别太大了,但是跟印度其实反而是有可比性的。
那我觉得印度我印象很深的是很多年前我在它北边一个邦,就是比哈,比哈邦是一个农业大省,比较穷困,但那边我就见到他们有一个运动,叫做民间科学运动。那这个民间科学运动其实它不只是个小学教育的东西,它是个全民的东西,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们发现所有过去的知识、学问、学术的教育的教材,很多时候都是由一些专业人士,可能是大学的研究者、学者,甚至是从外国直接翻译过来,然后他们再写出来或怎么样。那么比如说教科学认知的时候,教你对世界认识的时候,那个知识你会发现跟你身处的那个环境分别太大,他们那个城乡差距很大。
比如说我在比哈邦一个农村里面,我可能是睡帐篷的,在树底下挂个油布就当帐篷,一家人就睡那样的地方。然后我今天一翻开这个课本,课本里面跟我讲的就是人类探索月球的努力等等,那有时候学这个当然好,也开眼界。但是问题是他每天面对的问题就是我这个帐篷老漏水,我怎么来解决,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就发起一个运动,就是请一些学者、一些教育工作者跟一些社会工作者去看,这个地方的农民实际每天生活环境是什么,你每天遇到的是什么,然后从那里面整理出一些知识出来。比如说科学教育,或者数学知识,甚至是各种各样的知识,是能够从你的日常生活提炼出来,那孩子学的那个过程就是没有隔膜的。
他不会说,我明明住在比哈邦一个帐篷底下,你跟我说凡尔赛宫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也很好。但是我想先看看我这个地方我的生活环境是怎么样,它能不能知识化,他们做很多这种努力,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
周轶君:好,我们现在来回答一些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集他们有一些针对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印度这一集当中也谈到了爱的这个问题,就是印度人确实很友善,他们对孩子的宽容,我当中拍到有个台湾小孩到印度去感受到那种尊重和爱。
在这边我可以先插播我特别想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印度你知道满大街都是狗,野狗特别的多,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有的那种野狗,它是夏天趴在汽车轮胎下面,有一个人去开车的时候他往后倒车,然后就有点压到那个狗的前腿,然后那狗叫了一下,然后这时候全街道的人全部停下来,大家都来帮那条狗,都来关心看它有没有事,那狗后来也没事,它一瘸一拐走了。
但是我当时就是很感动,就是说他们没有因为很多的野狗,虽然他们有种姓制度,但没有觉得动物比他们低贱,真的会整条街的人停下来,那种感觉,包括印度那个孩子告诉我,他对自己国家的认知就是印度是个友爱的国家,陌生人之间会相互帮助。所以我们观众的问题他说很多孩子根本不明白,这个世界上最爱他们的可能只有他们的父母,他们想问你们,觉得孩子以后会明白父母对他们的爱吗?或者校长对他们的爱。
王世民:我想现在乡村的儿童,很多孩子现在这留守,他们可能懂得了奋斗,懂得了责任以后,他们是会理解的,父母离开家乡不是不爱他的表现,当他觉得他自己也有责任,他也有义务等等的时候,他可能会理解,父母这样做也是爱他另一种的一种表现,一种形式。
梁文道:我觉得因为中国,你别说留守儿童,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家长跟孩子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子时时贴在一起的亲密。就算中产阶级也常有这种问题,比如送小孩出去念书那种。所以这也是将来甚至对家庭是什么东西的一个重新的挑战,当你失去了这种物理空间的亲密性、接近性之后,家庭如何维持?
这个家庭如何维持不止是配偶如何维持,还包括两代人之间的感情如何维持,这个东西能不能透过像墙上的洞那样(改变),肯定是不能的,但这个很困难。
周轶君:我觉得每个人最后对爱的定义体验都很不同,你叫我自己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其实跟父母的关系一路走过来有很多的挣扎、反抗,像今天我看那些父母,比如说给孩子排满了所有的课,孩子有时候心里肯定也会讨厌的。
但是等你长大的时候有一天你回过头来想,我现在就发现中国的父母他们做的最好的一点真的是什么,他竭尽自己所能把最好的给孩子,不管他对不对,他真的是想把最好的给你,这个可能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我觉得有的父母甚至是做不到,中国父母的这种苦心我觉得全世界可能没有别人可以比。
我们下面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艺术教育的,有一位老师他是艺术培训机构的,他是舞蹈专业,可能是因为我们拍了关于在印度也有一些艺术方面的课程,他就说他认为目前大部分家长送孩子学艺术的目的是盲目的,他说也有的家长会认为学习不好才去学艺术,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在这种环境当中,在中国真正有效推行艺术教育,还有美育这些?
梁文道:我发现有一点很有趣,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社会底下,不论你在哪个地方的中国人社会,其实对于艺术教育的看法都很容易把它变成是用了学校的应试教育的模型来理解。比如说先问他到底有什么好处,学了之后有什么用,然后这时候就发现最管用的是干嘛,就是它可能最好要能考试,这个东西要是不能考试那就没什么用,比如说学钢琴那是能考试的,能考试就有成绩,有成绩就有奖状或者有证书。
周轶君:有奖状就安心了,表示学到了。
梁文道:表示学到了,而这个东西还真管用,因为将来说不定要读大学或者要干嘛的时候,好像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学生的履历。那么全往这个方向想,在我看来如果是这么想的话,这个艺术教育就等于是没用了,因为从头到尾那个孩子其实很讨厌这东西,他不喜欢。
王世民:我想不管是艺术教育其他方面这些教育,我觉得首先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特别是我们家长,这块不能从众。
周轶君:这太难了。
王世民:我就觉得这块家长首先还是要认识自己的孩子,要研究孩子的兴趣,他的特长是什么。因为每年一年一招生,一年级新生入学,我全部参加,这块跟他面谈。我问他一个问题,我就问孩子我说你喜欢喜欢什么,说老师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跳舞,我喜欢弹钢琴等等,100个一年级6岁的孩子,99个甚至100个他都会说我喜欢唱歌跳舞,我喜欢弹钢琴,几乎没有一两个孩子说我对计算很感兴趣,我对一些问题感兴趣。
周轶君:因为没有这个分类,他的兴趣班没有这个分类。
梁文道:不过换个角度想,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讲艺术教育太容易把它分割出来,变成一个专门的领域,其实不是这样。绝大部分的小孩子在他来讲学习、游戏,跟我们叫做艺术的东西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
一个小孩比如从幼儿园开始,他其实很多知识是在游戏中学会的,对他来讲画画或者用粘土捏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不单是艺术,我们太容易把它看成那是一种你怎么样才画得好,怎么样捏的像,不是,那还是一个他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他在掌握这个世界的造型,掌握他跟世界的关系。所以艺术其实是什么,小孩的艺术教育,我觉得绝对不能跟那种专业艺术教育混为一谈。
你教一个小孩子画画的目标不是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个画家,而是要给他一个他又玩的开心,在这个过程他在自由的探索什么叫颜色。
周轶君:是一个认知和表达的工具。
梁文道:对,它其实是个工具。
周轶君:下面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问你们两个都特别合适。他说国外存在隔代教育的问题吗?乡村有隔代教育的问题,文道更不用说了,你自己就是隔代教育长大的。
梁文道:对,我是隔代教育长大的。可能我这么长过来,我倒没觉得有多大问题,我小时候在台湾,我父母都在香港,我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基本上,但是还好我觉得。
周轶君:可能有问题也不自知了是吧?
梁文道:对,我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小学的时候运气很好,我上了一家我觉得非常好的小学。
周轶君:你有好的老师。
梁文道:对。但我那时候没寄宿,我是初中才寄宿,我小学的时候每天在学校时间很长,学校跟家的距离很远,我们要搭大巴的,我来回每天要两个多小时,在路上就跟同学们在玩什么,所以我花在学校的时间很长。
学校真的相当重要,因为小孩子的成长,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不是父母怎么对待他,当然这很重要,另一个地方就是你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同龄人的环境、伙伴环境,学校的伙伴环境对孩子的性格养成很重要。等于家里面的小孩如果有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互动对他影响很重要,他上学的时候他同学是怎么跟他相处,这种关系有时候其实比父母对他的关系可能说不定还重要。
周轶君:您觉得呢?
王世民:我觉得隔代教育这块其实现在在乡村,我觉得乡村教育也可以跟隔代教育画上等号,真的是大部分家长现在都不在身边,这个问题比如在我们学校这块怎么去化解,一个就是虽然说父母亲一年春节回来一次,但是现在技术很发达,互联网技术,让他们可以去视频等等的,定期的去跟家长多面对面的交流。
另外一个我们学校这块寄宿的孩子也比较多,这个也是一个规定吧,母亲一年要给孩子写六封信,一个学期三次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年春节前有一个全校的会,我们会对这个事情很看重的,就是跟孩子要去说。有的面对面的可能还不太好说,但是通过纸质文字可能还能把这个写出来。
第三个就是可以利用社区一些资源,一些义工,爱心人士这一块,他们在学校里帮他们整整床铺,跟他们有时候聊聊天,上午吃饭的时候有时候给他们打打饭。虽然这个不是他们的父母,但是孩子从小感觉这个社会是有很多人关心我的,爱我的,所以他们可能在这块这也就是一些无声的激励的教育,他可能成长得就更好一点。
第四个就是学校这一块,学校这块一定要把家庭的,父母的一些责任一些义务现在要勇敢地担当起来。你作为校长,你是老师,你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亲,以后就当成你自己的孩子去看。其实孩子留守,我觉得有时候工作如果到位的话可能那些不好的影响就大大的降低了。
周轶君:感谢两位的分享,我觉得在王校长这边我看到好多事情会有一些特别具体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非常好,要有想法还有办法。好,谢谢两位,我们下期再见。
梁文道:谢谢,谢谢王校长,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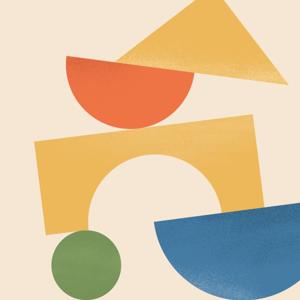

 View all episodes
View all episo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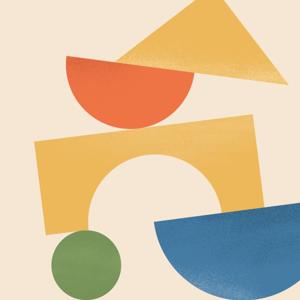 By 周轶君
By 周轶君